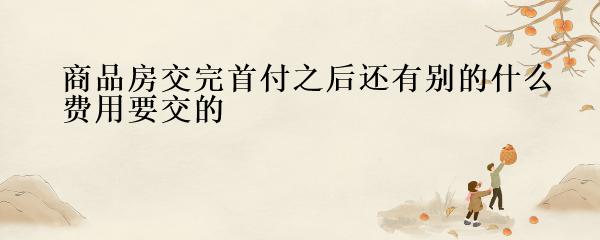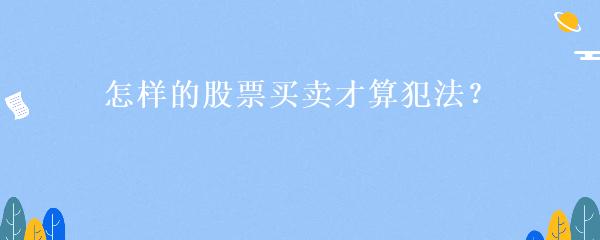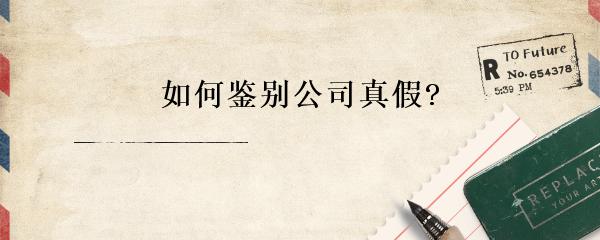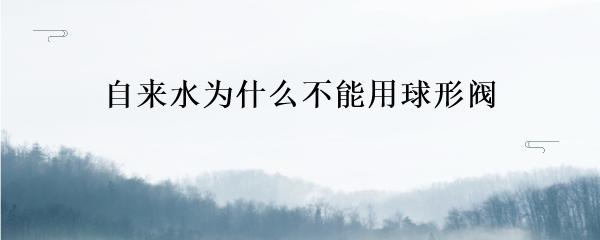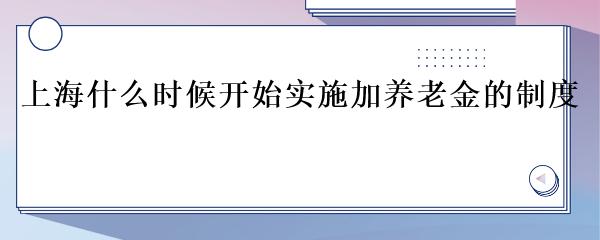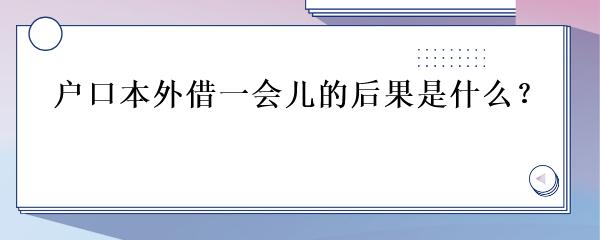首先,受胁迫而参加犯罪是胁从犯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在各共同犯罪人中获得最为宽大处罚的根本原因。而之所以胁迫能够对胁从犯的刑事责任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就在于它能够对行为人的精神造成一定程度的强制,使其因为惧怕自身利益的丧失或受到他人的现实侵害,而屈从于威胁实施犯罪。但是,我认为以侵害行为人非法利益为内容的威胁或强制,不应属于上述意义的胁迫。此种“胁迫”对行为人精神强制的程度,不足以达到刑法对胁从犯的构成要求。
作为非法利益的持有者,行为人应该明知自己的此种“利益”,如赃物、赌债、负案在逃现状等等,随时可能被国家、被害人或者其他人剥夺。所以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非法利益的丧失对行为人的精神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强制力,以及这种强制力是否足以达到刑法对成立胁从犯所要求的受胁迫程度,都存在疑问。换言之,从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角度,我认为,行为人在受到这种以侵害其非法利益为内容的“胁迫”时所产生的恐惧感,性质上属于其取得、持有非法利益这一先存事实而必然的附带后果。而具有通常智力和法律意识的行为人,应该对二者的这种因果关系存有明确的认识。故此时不论是相比那种侵害合法利益威胁所产生之恐惧的程度而言,还是行为人抗拒这两种恐惧拒绝犯罪的难度而言,上述两种胁迫的效果,差距都是十分明显的。相应地,前种情况成立胁从犯的合理性程度也要低的多。
其次,我国刑法对主犯、从犯和胁从犯,是采用按作用为主的标准进行分类。因此,确定胁从犯,我认为还是应该主要着眼于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这里所指的作用,也就是行为人实施犯罪给法益所造成的现实损害或危险状态。所以,如何衡量存在胁迫因素时犯罪行为使法益受到的危害程度,便成为确定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而判定胁从犯的关键。这里,我认为学者的以下见解值得参考:被胁迫的程度……与其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成反比例。被胁迫程度轻,说明他参加犯罪的自觉程度大一些;相反地,其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也要严重一些。据此,具体到因非法利益受侵害“胁迫”而犯罪的行为人,如前所述,其精神上受强制的程度微乎其微,远比合法利益受侵害威胁而实施犯罪的真正胁从犯具有更大的意志自由。因此从其行为对法益的危害程度来看,并不会因其受到此种“胁迫”而必然出现任何减轻的表现,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也不会因之而有所减弱。故将这种情况的行为人认作胁从犯处罚,有悖我国刑法对犯罪人分类的基本标准。对此,可能有人会认为:实践中受此种“胁迫”而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确属“情有可原”。而无视这种现实,仅以犯罪的法益侵害程度为标准,一概将行为人排除于构成胁从犯的可能之外,似有客观归罪之嫌。但是刑法学是规范学而不是事实学,什么样的因素是构成要件,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来确定,而不能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确定,也不能根据所谓“人之常情”来确定。





 微信
微信
 微博
微博
 QQ空间
QQ空间
 复制网址
复制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