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无效判决与撤销判决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界定是确认无效判决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把二者进行比较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如果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与救济的充分程度来考虑,确认无效和判决撤销对于当事人的意义实际无多大区别;从保证依法行政原则的角度观察,确认无效与撤销判决又都是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全面否定,力求恢复到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前的状态.因此,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确认无效和撤销判决之间并非互相排斥。甚至可以说,要对“无效”和“可撤销”的行政行为进行严格的区分,却绝非易事。那么,对于确认无效判决和撤销判决的关系,应当如何恰如其分地予以定位呢?如前文所述,《解释》中所增加的确认判决本身就是对行政诉讼法判决形式的补充。在司法实践中,当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经司法审查为违法时,撤销判决仍然是法官首选的方式。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家对此问题的处理方法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把确认无效判决视为“乘坐定期公共汽车”晚了点的撤销判决,确认无效判决与撤销判决之间是一种补充、转化关系对确认无效判决有了恰当的定位之后,就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它应该如何适用。一个可行的处理方式才能体现出确认无效判决的价值所在,并且弥补现阶段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的不足。笔者十分赞同这样的主张:在行政诉讼审判阶段,当行政行为的“无效”与“可撤销”之分没有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被提出时,法院可以甚至应当将其视为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处理.这样的处理结果同样可以达到确认无效判决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如此处理,还大大减轻了法官区分“无效”与“可撤销”的负担以及区分错误的风险。况且,在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制度化基本空白的境地下,这样处理具有现实意义。那么,余下的问题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无效”与“可撤销”之分,才会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首先,我们有必要确立确认无效判决独特的诉讼时效制度,即相对人请求法院作出确认无效判决时,不受现阶段的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作为替补性判决的确认无效判决理应在诉讼程序上与撤销判决有所区分,否则其完全可能被撤销判决所吸收。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无效行政行为非他,乃一类特殊的违法行为而已,若没有诉讼程序上的差别,确认无效判决完全可以为撤销判决或确认法判决所吸收,而无需其独立存在的形式.所以,当相对人在常规的起诉期限之外起诉时,确认无效判决就作为一种开拓救济手段而具有存在的意义,更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以及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简言之,相对人在常规的诉讼时效之外起诉的,确认无效判决成为一种必要。其次,如果相对人在常规的起诉期限之内起诉,而又明确提出请求法院作出确认无效判决时,确认无效判决也成为一种必要(法院审查后,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确属无效时)。这也是由“判与诉是相对应的,判决是对诉讼请求的回应”的理论使然。然而,与此同时,又产生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当相对人请求法院作出确认无效判决时,由谁来举证证明被诉行政行为无效呢?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解释》的相关规定,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当被告不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时,我们仅可以判断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却无法据此判断具体行政行为属于无效。因为,如前文所述,何为无效行政行为采取的是“重大且明显”说,无效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学上的特殊内涵是比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程度更加严重且明显的行政行为。其外延无法包括于一般违法行政行为之中.换句话说,我们尚不能通过被告的举证来推定具体行政行为无效。那么,证明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责任自然就落在相对人身上。诸多学者对无效行政行为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都作出了充分的论证,结果表明相对人承担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举证责任,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对此,笔者亦表示赞同。
 谁是谁的主角
2022-07-07
谁是谁的主角
2022-07-07  “所有者权益”包含哪些项目?
“所有者权益”包含哪些项目?所有者权益,即企业的净资产。其下包括的项目如下:
1、实收资本(或称:股本)——投资人的原始投入;
2、资本公积——资本的溢价部分和企业收到的捐赠等;
3、盈余公积——按《公司法》有关规定在税后利润中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和任意盈余公积金;
4、利润分配——利润分配后的留存收益,即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为股东权益。所有者权益是所有者对企业资产的剩余索取权,它是企业的资产扣除债权人权益后应由所有者享有的部分,既可反映所有者投入资本的保值增值情况,又体现了保护债权人权益的理念。
扩展资料:
所有者权益的来源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留存收益等。
利得或者损失。
其中:
利得(Gain)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分为:
(1)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
(2)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
损失(Loss)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分为:
(1)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损失;
(2)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损失。
 如果二次起诉需要什么手续1,需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2,本人向有管辖权法院立案时需要提交:(1)本人身份证件;(2)起诉状;(3)相关证据。3,起诉状中应当写明:(1)原、被告姓名、性别、联系方式;(2)诉讼请求,写明要求被告承担的责任、赔偿的项目;(3)事实与理由,简述事实,并针对诉讼请求中各项提出请求写明理由;(4)证据和证据来源,针对本人提出事实提供证据、证人,并注明来源及证人联系方式。4,《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百一十九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二十条 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第一百二十一条 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如果二次起诉需要什么手续1,需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2,本人向有管辖权法院立案时需要提交:(1)本人身份证件;(2)起诉状;(3)相关证据。3,起诉状中应当写明:(1)原、被告姓名、性别、联系方式;(2)诉讼请求,写明要求被告承担的责任、赔偿的项目;(3)事实与理由,简述事实,并针对诉讼请求中各项提出请求写明理由;(4)证据和证据来源,针对本人提出事实提供证据、证人,并注明来源及证人联系方式。4,《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百一十九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二十条 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第一百二十一条 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驾驶证分别能开什么车驾照。驾照是机动车驾驶证的简称,依照法律机动车辆驾驶人员所需申领的证照。驾照是一种证明,表明你具备了驾驶机动车需要的技能,可以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我国的驾照种类有:A类、B类、C类、D类、E类、F类、M类、N类、P类,其中A类、C类又分为3种,B类分为2种。2A1证。准驾车型为大型客车,可以开大型载客汽车和A3、B1、B2、C1、C2、C3、C4、M类车型。3A2证。准驾车型为牵引车,可以开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列车和B1、B2、C1、C2、C3、C4、M类车型。4A3证。准驾车型为城市公交车。可以开核载10人以上的城市公共汽车和C1、C2、C3、C4类车型。5B1证。准驾车型为中型客车,可以开中型载客汽车(含核载10人以上、19人以下的城市公共汽车)和 C1、C2、C3、C4、M类车型。B2证。准驾车型为大型货车,可以开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大、重、中型专项作业车和C1、C2、C3、C4、M类车型。C1证。准驾车型为小型汽车,可以开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以及轻型、微型载货汽车、轻、小、微型专项作业车和C2、C3、C4类车型。C2证。准驾车型为小型自动挡汽车,可以开小型、微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以及轻型、微型自动挡载货汽车C3证。准驾车型为低速载货汽车,可以开低速载货汽车(原四轮农用运输车)和C4类车型。C4证。准驾车型为三轮汽车,可以开三轮汽车(原三轮农用运输车)。D证。准驾车型为普通三轮摩托车,可以开发动机排量大于50ml或者最大设计车速大于50km/h的三轮摩托车和E、F类车型。E证。准驾车型为普通二轮摩托车,可以开发动机排量大于50ml或者最大设计车速大于50km/h的二轮摩托车和F类车型。F证。准驾车型为轻便摩托车,可以开发动机排量小于等于50ml,最大设计车速小于等于50km/h的摩托车。M 证。准驾车型为轮式自行机械车,只能开开轮式自行机械车。N证。准驾车型为无轨电车,只能开无轨电车。16P证。准驾车型为有轨电车,只可以开有轨电车。
驾驶证分别能开什么车驾照。驾照是机动车驾驶证的简称,依照法律机动车辆驾驶人员所需申领的证照。驾照是一种证明,表明你具备了驾驶机动车需要的技能,可以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我国的驾照种类有:A类、B类、C类、D类、E类、F类、M类、N类、P类,其中A类、C类又分为3种,B类分为2种。2A1证。准驾车型为大型客车,可以开大型载客汽车和A3、B1、B2、C1、C2、C3、C4、M类车型。3A2证。准驾车型为牵引车,可以开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列车和B1、B2、C1、C2、C3、C4、M类车型。4A3证。准驾车型为城市公交车。可以开核载10人以上的城市公共汽车和C1、C2、C3、C4类车型。5B1证。准驾车型为中型客车,可以开中型载客汽车(含核载10人以上、19人以下的城市公共汽车)和 C1、C2、C3、C4、M类车型。B2证。准驾车型为大型货车,可以开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大、重、中型专项作业车和C1、C2、C3、C4、M类车型。C1证。准驾车型为小型汽车,可以开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以及轻型、微型载货汽车、轻、小、微型专项作业车和C2、C3、C4类车型。C2证。准驾车型为小型自动挡汽车,可以开小型、微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以及轻型、微型自动挡载货汽车C3证。准驾车型为低速载货汽车,可以开低速载货汽车(原四轮农用运输车)和C4类车型。C4证。准驾车型为三轮汽车,可以开三轮汽车(原三轮农用运输车)。D证。准驾车型为普通三轮摩托车,可以开发动机排量大于50ml或者最大设计车速大于50km/h的三轮摩托车和E、F类车型。E证。准驾车型为普通二轮摩托车,可以开发动机排量大于50ml或者最大设计车速大于50km/h的二轮摩托车和F类车型。F证。准驾车型为轻便摩托车,可以开发动机排量小于等于50ml,最大设计车速小于等于50km/h的摩托车。M 证。准驾车型为轮式自行机械车,只能开开轮式自行机械车。N证。准驾车型为无轨电车,只能开无轨电车。16P证。准驾车型为有轨电车,只可以开有轨电车。 二婚经济如何处理好
二婚经济如何处理好双方都有子女的(都归自己抚养),现有财产平均分配,或者之前个自房产各归个子女,在一起后平均分配。当然了,收入高的一方也许会有一些意见,难免做不到。实在不行的话,就做个婚前的财产公证。最为重要的是,一切都要以现有家庭为主,二婚经济处理方式如下:
第一,把财产要划分阶段处理。
再婚女男婚前都会有一定的积累了,结婚前的财产和结婚后的财产要做好分割,不要混入婚后财产,要有凭证,要做个有心人,不要盲目的头脑发热,要看得长久一些。
第二,婚前财产做好财产公证。
虽然结婚的目的谁也不是为了离婚,可以事实上离婚率很高,那么离婚时为了财产不择手段的人很多,对自己的财产做好公证,是对自己的负责,彼此也要理解。
第三,婚后的经济双方要协商了。
如果都有工作,收入也比较稳定,是可以双方商定的,如果彼此特别信任,可以把工资放在一起,由一个人保管,出去日常开销,剩下的存款,或者投资。
第四,共同商量支出。
如果彼此收入差距较大,并且一方不同意把工资放在一起的话,可以商定每月共同拿出一定数目的钱作为日常开销,挣的多的可以适当多拿一点。一人买菜买米麦面,日常生活花费。
第五,双方都要学会存钱。
双方出钱每月有结余的话,可以自动存入下月,等到特殊日子出去搓一顿,改善生活。
第六,双方不能厚此薄非。
双方的老人,孩子也一定有各种花销的,可以双方共同拿钱,共同处理花费。一定不要厚此薄彼,关系才会处理得好,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扩展资料
建议:
一是情感上要互相依赖、互相信任,但在经济上还是不要太理想化,感情较好的,使用时可不分彼此,而权属上最好明晰。
二是居于此理,婚前财产最好分清,婚后财产可以共有,也可以大体上有所区分。
三是如有区分,可大体上明确各负责不同项目的开支,或者,各拿出一部分资金统一日常花销。特别是在对方有所防范或比较计较时更应好此。
当然,自己首先要从情感上接受这个现实,大家开诚布公地把话讲明应不会影响感情。否则,互相猜疑反而容易引起误会,影响感情,甚至于出现更严重后果。
 如何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如何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1、通过民主科学立法把公平正义的道德诉求法律化
立法通过民主的方式和法定程序,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分配权利与义务、明确权力与责任等实体性利益安排,通过立法规定相关程序、制定行为规则、划定行为界限、明确行为方式等等,实现通过立法分配正义的目的。
2、通过实施法律实现公平正义
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从以立法为中心转向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全面有效实施法律成为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心工作。
实施法律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环节,是实现立法公平正义宗旨和目的的具体体现,重点应当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自觉守法实现公平正义。
扩展资料:
法治社会追求的公正是一种相对的公正、程序的公正、规则的公正。法治社会主张事实的公正、结果的公正,但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实现这种公正;
法治社会追求权利的公正、机会的公正、规则的公正、过程的公正、程序的公正,只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切实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行、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做到良法善治和保障人权,就一定能够实现权利、机会、规则、过程和程序的公正。
法治社会追求的公正是具体的、相对的、有法律依据并能够得到法律程序保障救济的公正。在法治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应当抽象地主张公正,不应当脱离法律规则去追求公正,更不应当以破坏法治秩序的方式或者损害他人权利的方式去寻求公正的实现。
 微信二维码付款了,可以找到对方微信吗?
微信二维码付款了,可以找到对方微信吗?用微信二维码付款了并不能找到对方的微信账号,交易明细中只有交易单号、交易金额和交易时间等,并没有可以联系到对方的信息,具体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微信支付交易明细:
1、打开手机,打开手机中的“微信”,点击屏幕下方的“我”,找到“支付”:
2、打开支付,找到“钱包”:
3、打开钱包,找到“零钱”:
4、打开零钱,选择右上角的“零钱明细”:
5、打开零钱明细,找到一个交易记录,点击打开:
6、在打开的记录中,可以查看到具体的交易明细,包括交易金额、交易时间和交易单号等,并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所以没办法找到对方的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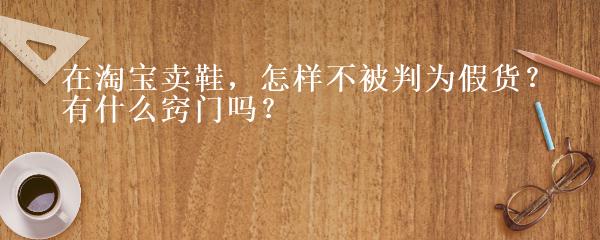 在淘宝卖鞋,怎样不被判为假货?有什么窍门吗?你卖的如果真的不是假货,那么只有和淘宝申述了,提交你卖的不是假货的证明,进货渠道,和品牌销售资格证书。判为假货通常都是系统检测 和人工举报。一般收到假货处罚通知 后台都是有说明的 。你按步骤走 申术 就可以了 。提交什么材料你就提交吧 。如果不是假货 会恢复的。还有类目 不要放错,价格不能高低幅度太大。照片不能用系统的 也不能用其它商家。标题也要符合产品,还有描述最好不要和其它同行相似。显示都是用数据包上传商品 ,弄的很多都是一样的图片 一样的描述。这样虽然方便 ,但是也很危险。 行了就说这些吧 ,有时候淘宝就是这样不清不楚的,其实漏洞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也很多,也许这就淘宝的思维 ,我们看似明白 其实一点也不明白。行了说这个你就不懂了 。你的销售的商品如果真的不是假货假冒的商品就申诉吧 ,别的没么敲门。
在淘宝卖鞋,怎样不被判为假货?有什么窍门吗?你卖的如果真的不是假货,那么只有和淘宝申述了,提交你卖的不是假货的证明,进货渠道,和品牌销售资格证书。判为假货通常都是系统检测 和人工举报。一般收到假货处罚通知 后台都是有说明的 。你按步骤走 申术 就可以了 。提交什么材料你就提交吧 。如果不是假货 会恢复的。还有类目 不要放错,价格不能高低幅度太大。照片不能用系统的 也不能用其它商家。标题也要符合产品,还有描述最好不要和其它同行相似。显示都是用数据包上传商品 ,弄的很多都是一样的图片 一样的描述。这样虽然方便 ,但是也很危险。 行了就说这些吧 ,有时候淘宝就是这样不清不楚的,其实漏洞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也很多,也许这就淘宝的思维 ,我们看似明白 其实一点也不明白。行了说这个你就不懂了 。你的销售的商品如果真的不是假货假冒的商品就申诉吧 ,别的没么敲门。 质量事故的处理程序质量事故处理的一般程序如下:发生事故后:1. 事故调查 项目负责人及时按法定的时间和程序报告事故,调查结果写成事故调查报告。2. 事故的原因分析 找出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3. 制定事故处理的方案 确定是否进行处理和怎么样处理4. 事故处理包括事故的技术处理和事故的责任处罚,对责任人和责任单位作出处罚5. 事故处理的鉴定验收处理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提交事故处理报告。
质量事故的处理程序质量事故处理的一般程序如下:发生事故后:1. 事故调查 项目负责人及时按法定的时间和程序报告事故,调查结果写成事故调查报告。2. 事故的原因分析 找出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3. 制定事故处理的方案 确定是否进行处理和怎么样处理4. 事故处理包括事故的技术处理和事故的责任处罚,对责任人和责任单位作出处罚5. 事故处理的鉴定验收处理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提交事故处理报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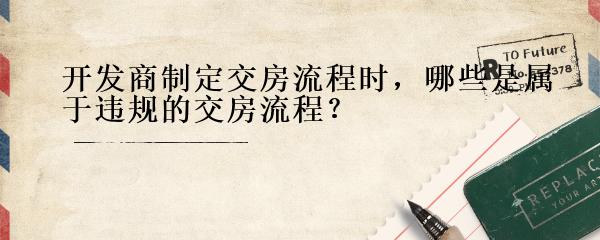 开发商制定交房流程时,哪些是属于违规的交房流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点:(1)以补交面积差价款作为房屋交付条件。一般在双方所签的补充协议中对房屋差价款的结算时间均有约定,但在纠纷时开发商往往不顾此约定,强行要求购房者交付面积差价款,并以此作为交房条件,如不交此款,开发商便拒绝交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该房是否具备交付条件,开发商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违约,因此而不能交付房屋的责任应完全由开发商承担。(2)以违规代收契税、维修基金作为房屋交付条件。
开发商制定交房流程时,哪些是属于违规的交房流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点:(1)以补交面积差价款作为房屋交付条件。一般在双方所签的补充协议中对房屋差价款的结算时间均有约定,但在纠纷时开发商往往不顾此约定,强行要求购房者交付面积差价款,并以此作为交房条件,如不交此款,开发商便拒绝交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该房是否具备交付条件,开发商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违约,因此而不能交付房屋的责任应完全由开发商承担。(2)以违规代收契税、维修基金作为房屋交付条件。 建筑工地怎么开收入证明可以找雇佣公司开具相关的收入证明并加盖公章。个人范本兹证明 为本单位职工,已连续在我单位工作 年,学历为 毕业,当前在我单位担任 职务。近一年内该职工在我单位平均年/月收入为(税后) 元,(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整)。特此证明:单位名称年 月 日个人收入证明的内涵 : 包括工资(一般指年收入总额)、养老保险缴费复印件、自有房产证明、私家车辆证明、大额定期存折复印件、外汇、债券、黄金有价证券帐户、大额人寿养老分红保单等。注意事项第一:开收入证明要注意必须的格式。第二:开收入证明必须要盖“鲜章”也就是收入证明复印是无效的。第三:盖的章必须是单位的财务章或者是单位的公章。而且必须是圆章。
建筑工地怎么开收入证明可以找雇佣公司开具相关的收入证明并加盖公章。个人范本兹证明 为本单位职工,已连续在我单位工作 年,学历为 毕业,当前在我单位担任 职务。近一年内该职工在我单位平均年/月收入为(税后) 元,(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整)。特此证明:单位名称年 月 日个人收入证明的内涵 : 包括工资(一般指年收入总额)、养老保险缴费复印件、自有房产证明、私家车辆证明、大额定期存折复印件、外汇、债券、黄金有价证券帐户、大额人寿养老分红保单等。注意事项第一:开收入证明要注意必须的格式。第二:开收入证明必须要盖“鲜章”也就是收入证明复印是无效的。第三:盖的章必须是单位的财务章或者是单位的公章。而且必须是圆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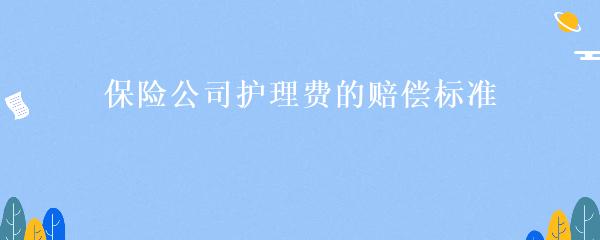 保险公司护理费的赔偿标准
保险公司护理费的赔偿标准护理费赔偿标准:
1、护理费的赔偿,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员的期限来决定的,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无收入的,指本人生活来源主要或者全部依靠他人供给或者有少量收入,但不足以维持本人正常生活的。
2、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支付护理费。构成伤残的护理费应为至定残前一日。
3、护理费赔偿计算公式为:人身损害发生地护理同等级别护理劳务报酬标准×护理天数×护理人数。关于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法律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工龄认定怎么认定?
工龄认定怎么认定?计算工龄的方法如下:
1、连续计算法,也叫工龄连续计算。例如,某职工从甲单位调到乙单位工作,其在甲、乙两个单位的工作时间应不间断地计算为连续工龄。如果职工被错误处理,后经复查、平反,其受错误处理的时间可与错误处理前连续计算工龄的时间和平反后的工作时间,连续计算为连续工龄。
2、合并计算法,也叫合并计算连续工龄。是指职工的工作经历中,一般非本人主观原因间断了一段时间,把这段间断的时间扣除,间断前后两段工作时间合并计算。如精简退职的工人和职员,退职前和重新参加工作后的连续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
3、工龄折算法。从事特殊工种和特殊工作环境工作的工人,连续工龄可进行折算。如井下矿工或固定在华氏32度以下的低温工作场所或在华氏100度以上的高温工作场所工作的职工,计算其连续工龄时,每在此种场所工作一年,可作一年零三个月计算。在提炼或制造铅、汞、砒、磷、酸的工业中以及化学、兵工等工业中,直接从事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职工,在计算其连续工龄时,每从事此种工作一年,作一年零六个月计算。
计算连续工龄的原则规定如下:职工发生以下情况,其前后工龄连续计算:
1.凡经企业管理机关、企业行政方面调动工作、安排下岗者,调动、下岗(与企业保持劳动关系)前后的工龄应连续计算;
2.经企业管理机关、企业行政方面调派国内外学习者,其学习期间以及调派前后的工龄应连续计算;
3.因企业停工歇业或者破产,职工经企业管理机关调派到其他企业工作者,调派前后的工龄应连续计算;
 图片原始拍摄日期如何查看
图片原始拍摄日期如何查看1、首先打开自己的电脑,然后在电脑里找到ps软件点击打开,在主界面点击文件然后点击在Bridge中浏览的选项。
2、点击Bridge中浏览的选项来到新的界面,这时就可以添加自己想要知道的原始拍摄日期的图片即可。
3、这时就进入新的界面了,添加图片之后,就可以看到原始日期时间了,很多具体报告模式,闪光灯,光源等都是可以看到的。
 水表怎么拆开擦拭
水表怎么拆开擦拭水表拆开步骤:
1、水表有一个铅的硬封印,只有专门的工具才能打开,可以请求别人或者找相关人士借用工具。
2、一般现在水表是不允许自行拆卸的,发现问题可以直接和水厂联系,需要更换的就更换,千万不要自己处理,这也是水厂不允许的做法的。
3、如果不是自来水厂安装的水表,可以先关掉总阀,把表盖打开,用毛刷顺着指针边冲边刷,干净后旋紧盖子即可。
4、当水表被拆卸下来之后,就可以用毛巾或者干的布把它擦干净,然后重新装上就行了。
扩展资料:
水表的使用注意事项:
1、智能水表需要更换电池,在更换之后记得将防潮该盖好,将螺丝拧紧,不然的话,智能水表是不会工作的。这样智能水表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
2、在长期不使用水的时候关闭上下游的阀门,不然容易造成智能水表的损坏,而且这种情况的损坏一般公司是不会负责的。
3、水表一定要之一防潮防冻,特别是在冬季,一定要对智能水表进行一定的保护措施。另外,如果出现这样的故障,即智能水表上的电子显示与实际的字轮不一样,出现计量错误的现象,我们要看实际字轮。
 公务员是党员的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工资待遇
公务员是党员的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工资待遇根据有关规定,党纪处分、政纪处分都是影响公职人员工资待遇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的大小也因处分轻重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党纪处分对工资待遇影响的原则性规定。公职人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处分时,必须降低一级以上的职务;受留党察看时,其职级和工资的降幅一般应大于相同职级撤职处分者;受开除党籍处分但未给予行政开除时,其职级和工资待遇的降幅一般大于相同职级受留党察看处分者。
第二,政纪处分对工资待遇影响的原则性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工资档次;受撤职处分的,应当按照规定降低级别。
第三,降低工资待遇的不同情形及规则。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含撤销党内职务和撤销职级待遇,下同)和行政降级以上(含降级)处分的人员,办理降低职务级别、降低工资手续。对上述人员的处分决定中未明确降低职务和降低工资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降低职务级别、降低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手续;对在党的机关工作的党员干部和在其他机关中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党务干部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处分的,参照国家相关规定,办理降低职务(含职级待遇)、同时降低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手续。
第四,各种处分对工资待遇的具体影响。受降级处分的人员,降低一级以上(含一级)级别工资,从处分的下月起按新级别发放工资;如果其级别工资在本职务已经是最低级别的,那么可以降低一档以上(含一档)职务工资档次。
受撤职处分,应同时降低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从受处分的下月起,其职务工资按新任职务同等条件大多数人员的工资水平重新确定,新确定的职务工资额应低于原任职务工资额;级别工资应降低一级(含一级)以上,若降低级别工资后其级别工资仍高于新任职务最高级别工资的,须按新任职务最高级别工资执行。
受开除处分的人员,自处分之日起,解除其与国家行政机关的人事行政关系,从受处分的下月起停发工资。
受行政记过以上处分的工作人员,解除处分后,其正常晋升工资的考核年限,从解除处分的下年起重新计算。
 失信人可以买社保嘛失信被执行人能交社保。对于失信被执行人,国家不会剥夺其工作的权利,而只要你有工作,工作单位就要给你交社保,这是国家的一种强制保险制度;另外,即使你没有工作,也是可以自己个人交社保的。需要提醒的是,失信被执行人虽然能交社保,但是会被限制各种高消费行为,如乘坐飞机、高铁,出入高档娱乐场所,甚至子女不能就读高收费的私立学校等。
失信人可以买社保嘛失信被执行人能交社保。对于失信被执行人,国家不会剥夺其工作的权利,而只要你有工作,工作单位就要给你交社保,这是国家的一种强制保险制度;另外,即使你没有工作,也是可以自己个人交社保的。需要提醒的是,失信被执行人虽然能交社保,但是会被限制各种高消费行为,如乘坐飞机、高铁,出入高档娱乐场所,甚至子女不能就读高收费的私立学校等。 有哪些形容“法官”的成语?
有哪些形容“法官”的成语?形容法官的词语: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执法如山、秉公办案、不徇私情、刚直不阿。 不畏权势、铁面无私、 明察秋毫、体恤民情。 正大光明、一视同仁、 有法必依,坚贞不屈。
【成语】: 两袖清风
【拼音】: liǎng xiù qīng fēng
【解释】: 衣袖中除清风外,别无所有。比喻做官廉洁。也比喻穷得一无所有。
【出处】: 元·陈基《次韵吴江道中》诗:“两袖清风身欲飘,杖藜随月步长桥。”
【举例造句】: 他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官,依然是两袖清风。 ★清·李宝嘉《文明小史》第十二回
【拼音代码】: lxqf
【近义词】:洁身自好、一贫如洗、廉洁奉公
【反义词】:贪得无厌、贪赃枉法
【歇后语】: 胳膊弯里打凉扇
【灯谜】: 马蹄服
【用法】: 作谓语、定语;指为官清廉
造句:
1、两袖清风是廉者的幸福,生意兴隆是商人的幸福,惩恶锄奸是侠士的幸福,品学兼优是学生的幸福,扶危济困是善人的幸福,春种秋收是农人的幸福。
2、廉而洁,一身正气;勤而俭,两袖清风。
3、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风雨。今天教师节,最是师恩难忘时,向所有教师送上诚挚的祝福!秋风拂面,凉意渐浓,秋日保健多喝蜂蜜少吃姜,秋燥远离您!
4、耐寂寞,两袖清风;讲公道,一身正气。
5、两袖清风,悬壶济世,平易近人,医人医心,仁心仁术。
6、一心为公自会宠辱不惊,两袖清风始能正气凛然。
7、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晴雨,加上五脏六腑,七嘴八舌九思十分用心,滴滴汗水诚滋桃李芳天下。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晴雨,加上五脏六腑,七嘴八舌九思十分用心,滴滴汗水,桃李芳天下!
8、一身正气,美于心灵,两袖清风,廉于行动。
9、三尺讲台三十教龄,两鬓斑白两袖清风。终觉教书自有佳境,绝知育人贵在冰心。
10、一支粉笔,写尽古往今来;两袖清风,堪称清正廉明;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在教师节来临之际,送上我最真诚的祝福:老师,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11、两袖清风,清白教书,身正令行,一世为范。
12、两袖清风身欲飘,杖藜随月步长桥。
13、慎言慎行一身正气清正廉洁两袖清风。
14、一身正气立身从教,两袖清风以德育人。
15、两袖清风诲莘莘学子,洁身自好树师德风范。
 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如何操作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操作方法:可以两种选择。第一,就是等着承兑汇票到期,拿到银行去兑成银行存款。对于到期日还有一段时间的承兑汇票,不推荐这样弄。第二,就必须转让当做钱付款给别人。第三、汇票的钱只能打到单位帐户上。
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如何操作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操作方法:可以两种选择。第一,就是等着承兑汇票到期,拿到银行去兑成银行存款。对于到期日还有一段时间的承兑汇票,不推荐这样弄。第二,就必须转让当做钱付款给别人。第三、汇票的钱只能打到单位帐户上。 怎样把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
怎样把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按照下列格式整理:
录音材料
录音时间:
录音地点:
在场人:(甲、乙...)
录音材料整理人:
录音内容
甲.......
乙.......
录音证据属于试听资料证据,在整理时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保留录音证据的原始资料;
第二,刻录成光盘提交法庭;
第三,形成书面的表现形式,将双方谈话内容以文字的行为表现出来;
第四,保持录音证据的完整,不要剪接。
扩展资料: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七十条规定的 “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是有证明力的。要使该录音证据成为判决依据,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其一,录音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录音双方当事人的谈话当时没有受到限制,是自觉自由的意思表示,是善意和必要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
其二,该录音证据录音技术条件好,谈话人身份明确,内容清晰,具有客观真实和连贯性,未被剪接或者伪造,内容未被改变,无疑点,有其他证据佐证。
 要怎么查证券户绑定了哪个银行卡?
要怎么查证券户绑定了哪个银行卡?在证券端可以看到绑定的银行,进入该银行的网上银行找到三方存管,看到绑定的证券公司就可以看到绑定的卡号了。
证券绑定的银行卡号在证券公司是查询不到的,证券公司只能看到是绑定了哪个银行,看不到具体卡号。如果该银行,投资者只有一张卡,那应该是就是这张卡了。如果投资者有多张卡,就只能通过银行端查询了。
扩展资料
随着证券市场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的深入,证券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拓展业务时采用的一系列手段措施,面临较大风险:
(1)向客户融资。由于向客户透支资金的方法已经被严厉禁止,变相透支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利用国债交易向客户融资等),有的还与银行共同协作,使融资行为不易被发现。
(2)返佣。返佣使经营成本加大,一旦行情不好,返佣成为节约费用的包袱;返佣的帐务处理有的返还现金,管理漏洞较多;返佣比例制定亦有较大的随意性,增加了规范管理的难度;同时返佣税金的收取有的只代扣了个人所得税,未扣所得税、营业税,留下了隐患。
 外出打工需要带什么
外出打工需要带什么身份证、现金、衣服、被褥、日常用品。
建议不要带太多东西,携带不方便,有可能丢失,可以到达目的地再买一些东西。
在车站之类人多的地方,要保护好贵重的东西。如果有同乡比较要好伙伴一起出来更好,可以互相照应。
扩展资料
居住情况:
1、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仍是以雇主或单位提供住宿为主
从近几年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居住情况的变化看,呈现出与他人合租住房比重上升、独立租赁住房比重下降的趋势,另一明显变化态势是务工地自购房比重下降、乡外从业回家居住比重上升。
2、四成外出进城务工人员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
从外出受雇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负担看,49.5%的进城务工人员由雇主或单位提供免费住宿;9.2%的进城务工人员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但有住房补贴;41.3%的进城务工人员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
 房地产经纪是什么房地产经纪是指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为促成他人房地产交易而从事居间、代理等经纪业务的经济活动。目前主要业务是接受房地产开发商的委托,销售其开发的新商品房。房地产经纪业务,不仅是代理新房的买卖,还包括代理旧房的买卖。
房地产经纪是什么房地产经纪是指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为促成他人房地产交易而从事居间、代理等经纪业务的经济活动。目前主要业务是接受房地产开发商的委托,销售其开发的新商品房。房地产经纪业务,不仅是代理新房的买卖,还包括代理旧房的买卖。 交警锁定车辆档案是什么意思
交警锁定车辆档案是什么意思锁定车辆档案是系统管理的一种手段,原因可能有法院查封、事故未处理等多种因素。被锁定的车辆不能年检,不能提档过户等等有关手续不能办理,也不能使用,需要去解锁。
在机动车登记系统里,车辆状态有以下几种:正常、违法未处理、锁定、强制报废等几种。
扩展资料:
如何解锁被锁定的车辆档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要求查封机动车档案的,应当出具公函。
车辆管理所应当从受理的当日起,暂停办理该车的各项登记业务。
车辆管理所接到原查封单位的公函,通知解封机动车档案的,应当立即予以解封,恢复该车的各项登记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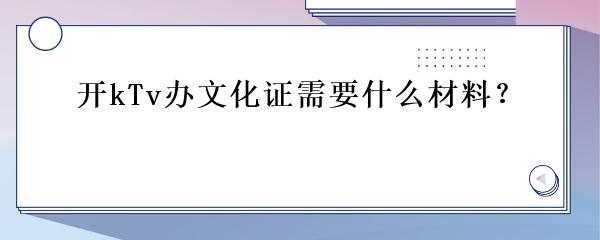 开kTv办文化证需要什么材料?
开kTv办文化证需要什么材料?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包括:
(一)、有效身份证及复印件;
(二)、所申请事项的申请书;
(三)、经营场地情况材料;
(四)、消防意见书;(网吧、娱乐业)
(五)、环保评估意见书;(娱乐业)
(六)、文化市场法规培训合格证。
扩展资料:
文化部关于实行《文化经营许可证》制定的规定
为了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严格执行文化经营许可证制度,现就各种文化经营活动实行《文化经营许可证》制度的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凡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取得收入或利用文化场所取得收入的经营活动,均为文化经营活动。
二、凡开办文化娱乐、美术品、音像、演出、业余文化艺术培训等文化经营活动,在申请工商登记注册前,必须报经所在县市以上(含县市)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领取《文化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三、《许可证》有效期为一年。有效期满后,持证单位或个人须向原发证部门申请核验换证
四、《许可证》的式样,由文化部统一规定印制。《许可证》分正本和副本。正本为悬挂式,副本为折叠式。
五、按规定取得《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必须依法经营,并接受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
六、按规定取得《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在经营活动中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注重社会效益,向人们提供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
七、《许可证》只限申报经营的单位或个人使用,不得转借、出租或出售。
八、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许可证》的管理,严格按条件审批发放。
九、以前的有关规定,凡与本规定有抵触的,按本规定执行。
十、本规定由文化部负责解释。
十一、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农商行有哪些部门,哪些部门比较好?农信社部门和职位
农商行有哪些部门,哪些部门比较好?农信社部门和职位
基层:普通柜员兼大堂经理、信贷内勤、信贷员、主管会计或内务主任、信贷副主任、网点负责人或主任。
联社机关:科员、副科长、科长、(分财务科、信贷科、风险科、综合人教科、监查审计科、资金营运科、清算中心科、后勤保障科、调研科)。
联社机关理事会或党委成员:四把手监事长、三把手财务副主任和综合人教副主任、二把手信贷主任、一把手理事长。
农村信用社内部部门
1、基层信用社主任岗
内勤主任岗
外勤主任岗(有的不设)
内勤岗位,包括会计主管、会计、储蓄、出纳、事后监督等岗位,其中某些岗位有的社不设或兼任。
外勤岗位,包括存量岗客户经理(主管企业贷款,其实没多大权力,但风险较小)部分地方已撤销存量岗,企业贷款收归县级联社管理。小额贷款客户经理(主管小额农户贷款,权力可大可小,视地区管理制度而定,风险较大)。
2、县级联社理事长岗
主任岗
监事长岗
副主任岗
各科室(部)科长(或经理、部长等名称),主要包括信贷科(有的叫风险管理部等名称,对信贷事务整体负责)、公司业务部(主管企业贷款的调查与管理,有的联社没有。)、人事科、综合科、行政科(有的联社三者合一,主管人事、文秘、后勤等)、安全保卫科、审计(稽核)科(主管辖内审计)、会计科、、电脑科、事后监督(这个部门有的归会计科管)、工会、理事长办公室等等部门,具体称呼视联社性质而定。(如信用联社、农商行、农合行等等)但职责差不多。
各科室办事人员。
3、市联社目前大多是省联社的办事处,岗位设置与县联社差不多。
4、省联社理事长、主任、副主任、监事长、办公室、人事教育处、计划统计处、信贷管理处、财务会计处、科技处、稽核处、监察保卫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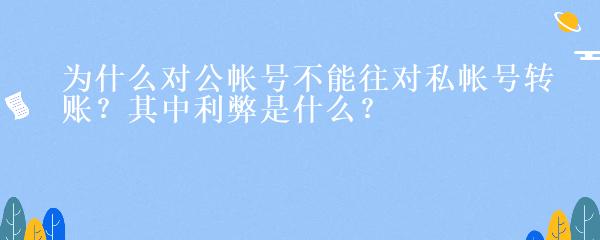 为什么对公帐号不能往对私帐号转账?其中利弊是什么?
为什么对公帐号不能往对私帐号转账?其中利弊是什么?为了确保资金安全。
利:
确保公司资金安全,防止个人挪用,另一个就是税收方面的考虑,确保利润结算的准确性。
弊:资金周转程序会比较繁琐,浪费时间。
公司对公帐户分为四类:基本帐户、一般帐户、临时帐户及专用帐户。
其中: 基本帐户一个公司只能开一个。
一般帐户:一个公司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开立多个,没有数量限制。
扩展资料:
公对公转账分为同行转账,以及跨行转账。
转账到账时间参考:同行之间转账即时到账。
跨行转账需要时间参考:
1、选择快速到账,一般为实时到账,延迟不超过2小时;
2、跨行交易因为要通过双方银行柜台进行业务处理,一般要一至三个工作日才能到账;
3、如果是周五晚上转的帐,最早下周一到账,最迟周三到账;
4、周一到周五白天下午三点前转账基本能当天到对方银行,但对方银行是否及时入账决定到账实际时间。
5、银行卡同一系统即时到账。
 支付宝别人发给我的红包为什么领不了如果不是对方设置了什么领取条件,你没有达到,就是你的账户本身出了问题。现在的支付宝账户都要求实名认证。如果你的账户还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很多实名认证受限的。
支付宝别人发给我的红包为什么领不了如果不是对方设置了什么领取条件,你没有达到,就是你的账户本身出了问题。现在的支付宝账户都要求实名认证。如果你的账户还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很多实名认证受限的。 树木买卖需要些什么证件树木买卖一般有具有经营权的单位依法进行,由卖方为买方办理运输证明;出口木材应办理检疫证。没有经营权应办理销售木材的砍伐证和运输证。农民的散木销售应提供乡镇林业部门的证明。
树木买卖需要些什么证件树木买卖一般有具有经营权的单位依法进行,由卖方为买方办理运输证明;出口木材应办理检疫证。没有经营权应办理销售木材的砍伐证和运输证。农民的散木销售应提供乡镇林业部门的证明。 打对方电话总是无人接听是为什么?
打对方电话总是无人接听是为什么?一般是对方没有接听电话,所以用别的电话也是展示无人接听。
可能的情况是对方没在电话旁,或者听到有原因故意不接电话,或者看到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所以不接电话。
黑名单把来电号码设置为自动拒接。呼叫限制是打出的电话的目的地的范围限制。
扩展资料:
电话占线的解决方式:
可以通过如下几个方案测试
1、首先重新启动 MODEM ,一般会恢复正常,如果仍然不行建议重新启动计算机。
2、可以通过多次重拨 ADSL 的方式进行测试。
注:在连接属性的“选项”中能够实现自动重拨
2、可以把 MODEM 复位(一般 MODEM 上都有 reset 按钮),同时建议用户检查连线,重新启动计算机。
3、在命令行下运行如下两个命令 ipconfig /renew 和 ipconfig /release ,通过这种方式释放IP地址。
4、如果通过以上方式仍然无法解决,则可能电信运营商服务器或者网络线路问题,建议用户更换时段测试,无效联系电信运营商。
 苏州落户具体需要哪些条件啊?
苏州落户具体需要哪些条件啊?苏州落户具体条件如下:
一、有来苏就业意愿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在人事档案转入后可申请办理落户:
1、在国(境)外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并取得国家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的留学人员;
2、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及学士学位以上人员;
3、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




 微信
微信
 微博
微博
 QQ空间
QQ空间
 复制网址
复制网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