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法经营罪无限扩张的质疑与反思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中的非法经营罪已变成了这样一种罪名:对任何经营行为,只要被认为是挑战了行政垄断权(即所谓违反国家规定),都可以定罪处罚。但是,这种设计已超越了一般的简单罪状与空白罪状应有的界限,它所具有的适应性和包容量是以规范内容的模糊性、不明确性为代价的。这种做法是与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严重相悖的,其合理性值得怀疑。(一)无限扩张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选择背道而驰由于立法者自身的局限性,《刑法》的规范对象具有不完整性,故刑事立法不可能将所有应予刑罚制裁的不法行为毫无遗漏地加以规范,所谓刑法结构的严密性永远都只有相对意义。在现代法治原则确立以后,面对这一现实,立法者都选择承认刑法规范对象的不完整性,为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权而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罪刑法定消灭不了刑法的不完整性,而是以容忍刑法的不完整性的客观存在为其前提”[21]。罪刑法定原则使刑法本身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规则体系,它不允许在刑法规范之外对尚未明确规定的行为加以刑罚处罚,即使这一行为的确存在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这一原则本身具有限制机能,它限制了刑法过分干预社会生活,是立法者价值偏一的选择。然而,《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却使非法经营罪成为一个“超级的”概然性条款,一个新的“口袋罪”,它所拥有的巨大的扩张性在本质上使其同类推制度具有同样的价值取向,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形式上尚披着罪刑法定的外衣。(二)非法经营罪的设立使刑罚权存在滥用的危险贝卡利亚曾指出,法律的含混性是一个弊端,它会把法律这样“一部庄重的公共典籍变成一部家用私书”[22]。虽然立法是从千姿百态的事实中抽象出适用于所有案件的法律原则,肯定具备一定的概括性,但立法所设立的规范又必须具有相对的明确性。因为刑法规范既是评价规范,又是行为规范,它通过对禁止性行为的明确规定对社会公众的行为起引导作用。因此,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不仅要求罪刑规定事先由法律给出,更要求这种法律规范必须明确规定禁止性行为的客观特征,否则,模棱两可的法律规范会使人们无法把握法律的意旨,无所适从。这种法律规范,即使罪刑是法定的,但因其内容不明确,故也无法防止刑罚权的滥用,罪刑法定主义保障公民自由的目的也就无从实现。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和《刑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符合该条第一、二项除外)关键有两个要件。一是行为是否具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危害后果。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量化标准,故行为是否符合这一条件实际上是由司法机关自由裁量。二是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即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由于刑法并未指明确认该罪具体应参照哪些法律、法规,因此,在适用该条时,具体参照何种规范性文件事实上也由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自行决定,只要所参照的文件属于“国家规定”所涵盖的范围之内,其适用活动就是合法的。刑法的这一规定在适用上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是严重的。就司法解释而言,非法经营罪的这一规定事实上为司法权超越立法权提供了条件。
 以微笑面对
2022-06-04
以微笑面对
2022-06-04  开发商需要办完什么手续才能办房产证
开发商需要办完什么手续才能办房产证开发商办理房产证主要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是办“大证”,即初始登记,第二个就是办“小证”,即转移登记。权属登记通常先由开发商完成初始登记,之后才由各个买受人分别办理商品房买卖登记。办理初始登记须由开发商单方面提出申请,当商品房竣工后,开发商需将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证明、房屋已竣工的证明、房屋测绘报告等材料准备好,并提交给权属登记部门,之后取得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的收件单,这时初始登记办证的义务视为完成。办理完初始登记后,开发商和业主需共同提出转移登记申请,并提交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书、房屋买卖合同等材料,为业主办理转移登记是在开发商办理初始登记后的登记环节。另根据有关规定在办理转移登记前,业主应先缴纳契税和维修基金等相关税费。最后按规定领取房产证即可。
 土地产权政策的作用土地产权是指权利人在其权利存在的土地上,为实现其利用土地的目的,分别依法行使其权利时对土地的用益、流转、管理权。确立土地产权制度,明晰土地产权权利内容,在调整土地法律关系上有其重要作用。土地产权制度是土地管理制度的基础和依据。我国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是决定性的原因。从解决土地管理的根本问题出发,就必须从产权问题入手,抛开意识形态的羁绊,研究在现阶段,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采取既能提高效率又能实现公平的土地产权制度,继而解决土地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土地产权制度并轨,即农村土地国有化,赋予农户土地使用权,同时也取消城市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对正在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我国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1、土地国有化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基础和条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以“均田”作为施政纲领,但都有始无终,因其不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且没有抑制土地兼并的手段。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允许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发生。国家掌握了土地所有权,就能从根本上抑制对土地的兼并和垄断,制约个人或利益集团利用土地牟取暴利的情况发生。国家通过所有权可对土地利用、土地市场、土地收益进行掌控,使之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和手段。2、土地使用权长期化可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基础土地具有天然性和不可转移性,因此,它不是一般的商品。但土地具有排他性和有用性,因此,又具有商品的特性。为了有效地利用土地,使其优化合理地配置,按照市场原则,通过市场交易决定土地利用,较之于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实践证明是更为正确的选择。赋予利用者长期使用权,便使根据价值规律进行流转成为可能,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使单位土地有更大的产出。由于通过土地使用权对利用者的权益给予法律上的有效保护,可以鼓励利用者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从而改善土地的质量和环境。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土地通过行政手段配置。一旦项目获得批准,就可以通过无偿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一方面,虽具有降低投资成本继而降低产品成本的作用,但土地价值却没有在产品价值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无偿取得,土地占用最大化便成为理性的选择,土地的粗放利用便不可避免。土地不可思转让或只允许无偿转让,使大量土地占而不用,造成极大浪费,城市土地国有制演变成单位所有制。改革开放后,虽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但由于法律设定了最长70年的期限,致使土地的未来收益与成本的不确定性增加,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土地的流转和使用权价格的形成。实行土地使用权永久化,可消除未来土地成本的不确定性,土地市场就能够很快形成,其使用权价格将趋向合理化。3、 赋予农户长期土地使用权将对农民利益起到根本保护作用农户取得长期土地使用权不仅使用地农民的用地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使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使土地使用权成为农户既可以使用卫转让,又可以继承和抵押的资产,并可有效地制约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及村干部滥用权力。土地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只能依法对土地利用行使监督的权力,而不再有配置的权力。地方政府及村级组织再无资格参与对土地收益的分割,土地被征用后的补偿也将全额归农民所有。
土地产权政策的作用土地产权是指权利人在其权利存在的土地上,为实现其利用土地的目的,分别依法行使其权利时对土地的用益、流转、管理权。确立土地产权制度,明晰土地产权权利内容,在调整土地法律关系上有其重要作用。土地产权制度是土地管理制度的基础和依据。我国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是决定性的原因。从解决土地管理的根本问题出发,就必须从产权问题入手,抛开意识形态的羁绊,研究在现阶段,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采取既能提高效率又能实现公平的土地产权制度,继而解决土地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土地产权制度并轨,即农村土地国有化,赋予农户土地使用权,同时也取消城市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对正在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我国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1、土地国有化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基础和条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以“均田”作为施政纲领,但都有始无终,因其不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且没有抑制土地兼并的手段。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允许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发生。国家掌握了土地所有权,就能从根本上抑制对土地的兼并和垄断,制约个人或利益集团利用土地牟取暴利的情况发生。国家通过所有权可对土地利用、土地市场、土地收益进行掌控,使之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和手段。2、土地使用权长期化可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基础土地具有天然性和不可转移性,因此,它不是一般的商品。但土地具有排他性和有用性,因此,又具有商品的特性。为了有效地利用土地,使其优化合理地配置,按照市场原则,通过市场交易决定土地利用,较之于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实践证明是更为正确的选择。赋予利用者长期使用权,便使根据价值规律进行流转成为可能,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使单位土地有更大的产出。由于通过土地使用权对利用者的权益给予法律上的有效保护,可以鼓励利用者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从而改善土地的质量和环境。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土地通过行政手段配置。一旦项目获得批准,就可以通过无偿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一方面,虽具有降低投资成本继而降低产品成本的作用,但土地价值却没有在产品价值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无偿取得,土地占用最大化便成为理性的选择,土地的粗放利用便不可避免。土地不可思转让或只允许无偿转让,使大量土地占而不用,造成极大浪费,城市土地国有制演变成单位所有制。改革开放后,虽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但由于法律设定了最长70年的期限,致使土地的未来收益与成本的不确定性增加,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土地的流转和使用权价格的形成。实行土地使用权永久化,可消除未来土地成本的不确定性,土地市场就能够很快形成,其使用权价格将趋向合理化。3、 赋予农户长期土地使用权将对农民利益起到根本保护作用农户取得长期土地使用权不仅使用地农民的用地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使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使土地使用权成为农户既可以使用卫转让,又可以继承和抵押的资产,并可有效地制约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及村干部滥用权力。土地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只能依法对土地利用行使监督的权力,而不再有配置的权力。地方政府及村级组织再无资格参与对土地收益的分割,土地被征用后的补偿也将全额归农民所有。 塔吊产权怎样过户如何办理塔吊备案登记产权单位新购买塔机(含购买二手设备)后,首次出租或使用前,需要到区县建委办理登记备案,获得登记编号。登记备案的具体办理程序如下:一、本地企业办理登记备案工商注册地再北京的本地企业办理登记备案的程序如下:(一)、网上申请登记编号企业购买新塔机(含购买二手设备)后,登录北京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上办公大厅进行登记编号申请,对新购塔机要填写生产厂家、出厂编号、设备原值、型号等详细信息,进行申报即可完成网上登记编号申请。(二)、到区县建委现场办理登记备案:网上登记编号申请成功后,需要到企业注册所在地所属的区县建委办理登记备案,区县建委核对原件,留存复印件,所有资料复印件应当加盖产权单位法人公章,产权单位提供资料如下:1、北京市其中机械登记备案表;2、起重机械产权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个体营业执照不能办理登记编号);3、起重机械购置合同及发票或者能证明产权的资料(分期付款购买的塔机凭合同和首付款收据办理);4、产品合格证;5、生产企业的“特殊设备制造许可证”;6、2006年10月1日后出厂的塔机需提供“制造监督检验证明”。注:如购买的是二手塔机,还需提供原产权单位的登记编号或原始购买合同和发票,同时原单位注销原登记编号。(三)、区县建委审核合格后,颁发统一编号证书区县建委再审核后,五个工作日内为产权单位办法统一编号证书。二、外地企业办理登记备案工商注册地再外地的产权单位,需要到企业注册地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起重机械登记备案,获得登记编号。塔机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首次出租或使用前,产权单位首先要到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上办公大厅进行注册,获得用户名和密码,然后进入起重机械备案系统中“外地起重机械登记编号备案”栏目,输入设备相关信息,提交到首次出租或使用工地所在地的区县建委。区县建委核实登记编号元件(由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并从网上确认后,登记编号信息即可进入“北京市起重机械备案系统”数据库。此后,该台设备在北京市办理安装(拆卸)告知、使用登记、检测等手续时,与本地企业的设备办理程序基本相同。
塔吊产权怎样过户如何办理塔吊备案登记产权单位新购买塔机(含购买二手设备)后,首次出租或使用前,需要到区县建委办理登记备案,获得登记编号。登记备案的具体办理程序如下:一、本地企业办理登记备案工商注册地再北京的本地企业办理登记备案的程序如下:(一)、网上申请登记编号企业购买新塔机(含购买二手设备)后,登录北京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上办公大厅进行登记编号申请,对新购塔机要填写生产厂家、出厂编号、设备原值、型号等详细信息,进行申报即可完成网上登记编号申请。(二)、到区县建委现场办理登记备案:网上登记编号申请成功后,需要到企业注册所在地所属的区县建委办理登记备案,区县建委核对原件,留存复印件,所有资料复印件应当加盖产权单位法人公章,产权单位提供资料如下:1、北京市其中机械登记备案表;2、起重机械产权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个体营业执照不能办理登记编号);3、起重机械购置合同及发票或者能证明产权的资料(分期付款购买的塔机凭合同和首付款收据办理);4、产品合格证;5、生产企业的“特殊设备制造许可证”;6、2006年10月1日后出厂的塔机需提供“制造监督检验证明”。注:如购买的是二手塔机,还需提供原产权单位的登记编号或原始购买合同和发票,同时原单位注销原登记编号。(三)、区县建委审核合格后,颁发统一编号证书区县建委再审核后,五个工作日内为产权单位办法统一编号证书。二、外地企业办理登记备案工商注册地再外地的产权单位,需要到企业注册地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起重机械登记备案,获得登记编号。塔机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首次出租或使用前,产权单位首先要到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上办公大厅进行注册,获得用户名和密码,然后进入起重机械备案系统中“外地起重机械登记编号备案”栏目,输入设备相关信息,提交到首次出租或使用工地所在地的区县建委。区县建委核实登记编号元件(由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并从网上确认后,登记编号信息即可进入“北京市起重机械备案系统”数据库。此后,该台设备在北京市办理安装(拆卸)告知、使用登记、检测等手续时,与本地企业的设备办理程序基本相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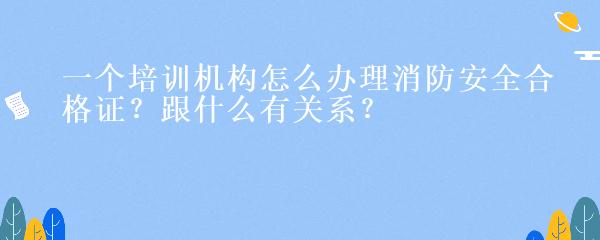 一个培训机构怎么办理消防安全合格证?跟什么有关系?
一个培训机构怎么办理消防安全合格证?跟什么有关系?去当地公安局申请,而且必须经过消防安全业机构培训合格。
申办材料:
(一)应填写文化娱乐场所消防安全审批表;
(二)凡新建场所要出示《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三)疏散指示标志和火灾事故照明灯等消防产品应出示该产品消防合格证;
(四)可燃装修进行阻燃处理时要出示检验报告及消防产品合格证;
(五)具有建筑消防设施的场所出示检测合格的《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六)洗浴场所应出示锅炉产品检验合格证;
(七)歌舞娱乐场所容纳的消费者不得超过核定人数。
审批范围及签发
(一)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 (不含有 2000 平方米 )以下的公共娱乐场所,由当地消防科(大队)负责审核发放消防安全许可证。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除外。
(二)建筑面积超过 2000 平方米 以上的,由支队负责审核发放消防安全许可证。
申办材料:
(一)应填写文化娱乐场所消防安全审批表;
(二)凡新建场所要出示《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三)疏散指示标志和火灾事故照明灯等消防产品应出示该产品消防合格证;
(四)可燃装修进行阻燃处理时要出示检验报告及消防产品合格证;
(五)具有建筑消防设施的场所出示检测合格的《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六)洗浴场所应出示锅炉产品检验合格证;
(七)歌舞娱乐场所容纳的消费者不得超过核定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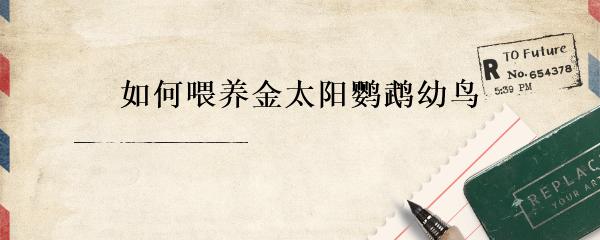 如何喂养金太阳鹦鹉幼鸟喂养金太阳鹦鹉雏鸟需要注意七个好:1、每天定时定量消化好要依照幼雏出生的天数不同,再视其消化状态,每日约需喂食数餐。约两周左右雏鸟,每两到三小时需喂食一次,三周左右的雏鸟,则每四小时依照消化状态喂食一餐,一个半月以上的雏鸟可以改为一日四餐;当雏鸟长成约两个月左右,除了一日喂食三餐以外,也可以给予些泡软的合成鸟粮或是滋养丸放置宠物的箱内,让它们无聊时顺便练习如何进食半糊状的食物,以便为将来进食干料预作准备。2、奶粉温度浓度控制好喂食雏鸟时,最好准备一支温度计,鹦鹉奶粉的温度以摄氏 39 到 40 度为佳,绝对不能超过摄氏 42 度,因为过热的温度会烫破幼鸟嗉囊,使其无法进食而死亡。给与的浓度依鸟的年龄有所不同,年龄越小越稀为好,太稠的奶粉会造成幼鸟无法消化,无法排空嗉囊,使得内部食物发酵形成嗉囊炎。3、喂食只喂七至八分好开始喂食时候,可用手轻轻的扶住幼鸟的头加以固定,然后轻柔的将汤匙靠近幼鸟的鸟喙,幼鸟便会主动索食。不用大口强灌幼鸟,以免食物误入幼鸟气管。观察幼鸟的嗉囊约7到8分饱时,就该停止喂食,不可硬撑强灌幼鸟,否则会造成幼鸟呕吐引发其他病变。4、奶粉质量新鲜够用好每次喂食幼鸟都应该调和新鲜且适量的奶粉,不要贪图方便一次调和过多份量,也不可以怕浪费而将本次喂剩下的奶粉留待下一餐食用。喂食完毕后,需用温水沾湿的棉花棒或是卫生纸等将沾在幼鸟鸟喙以及羽毛上的奶粉残余物擦拭干净,避免奶粉硬化将羽毛纠结在一起,或是引来蚂蚁或是小虫等造成卫生问题。5、喂食方法安全健康好喂食的食材有自制的鹦鹉奶粉或进口品牌的鹦鹉奶粉,里面包括细磨成粉状的谷类,再添加蛋白质、维生素或是消化酵素等,喂食幼雏可用幼鸟“专用汤匙”,其造型和一般汤匙不同,而是模仿亲鸟的鸟喙形状,使得幼鸟在进食流质时,易于进入口中而不会从四周流出。6、针筒喂食排净空气好针筒软管理喂食也是常见的方式,但是危险性相对较高。因为针筒在吸进液体时会有残留的空气储存于顶端,此时如果连空气一起注射入幼鸟的口中,针筒中残留顶端的空气会将幼鸟呛死,因此在使用针筒喂食前,一定要将其顶端的空气先排净,然后轻轻的推入幼鸟的口中,避免针筒刺伤幼鸟的舌头或是口腔。而软管喂食通常容易误插入幼鸟的气管内导致窒息而死。所以新手绝对不要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任意使用,否则很容易造成爱鸟死亡。7、断奶方法循序渐进好当健康状况良好的幼鸟接近2个半月大,出现索食意愿不强烈甚至拒食的情况时,可以准备糊状或是干料来训练教导幼鸟离乳。离乳期间可以采取少量多餐的方式给与幼鸟较稀的奶粉补充体力,过程必须循序渐进,不可立即断绝手喂鹦鹉奶粉而强迫其进食干料,否则幼鸟很可能会因为自己不会进食或是进食的份量不足而导致营养不良死亡。
如何喂养金太阳鹦鹉幼鸟喂养金太阳鹦鹉雏鸟需要注意七个好:1、每天定时定量消化好要依照幼雏出生的天数不同,再视其消化状态,每日约需喂食数餐。约两周左右雏鸟,每两到三小时需喂食一次,三周左右的雏鸟,则每四小时依照消化状态喂食一餐,一个半月以上的雏鸟可以改为一日四餐;当雏鸟长成约两个月左右,除了一日喂食三餐以外,也可以给予些泡软的合成鸟粮或是滋养丸放置宠物的箱内,让它们无聊时顺便练习如何进食半糊状的食物,以便为将来进食干料预作准备。2、奶粉温度浓度控制好喂食雏鸟时,最好准备一支温度计,鹦鹉奶粉的温度以摄氏 39 到 40 度为佳,绝对不能超过摄氏 42 度,因为过热的温度会烫破幼鸟嗉囊,使其无法进食而死亡。给与的浓度依鸟的年龄有所不同,年龄越小越稀为好,太稠的奶粉会造成幼鸟无法消化,无法排空嗉囊,使得内部食物发酵形成嗉囊炎。3、喂食只喂七至八分好开始喂食时候,可用手轻轻的扶住幼鸟的头加以固定,然后轻柔的将汤匙靠近幼鸟的鸟喙,幼鸟便会主动索食。不用大口强灌幼鸟,以免食物误入幼鸟气管。观察幼鸟的嗉囊约7到8分饱时,就该停止喂食,不可硬撑强灌幼鸟,否则会造成幼鸟呕吐引发其他病变。4、奶粉质量新鲜够用好每次喂食幼鸟都应该调和新鲜且适量的奶粉,不要贪图方便一次调和过多份量,也不可以怕浪费而将本次喂剩下的奶粉留待下一餐食用。喂食完毕后,需用温水沾湿的棉花棒或是卫生纸等将沾在幼鸟鸟喙以及羽毛上的奶粉残余物擦拭干净,避免奶粉硬化将羽毛纠结在一起,或是引来蚂蚁或是小虫等造成卫生问题。5、喂食方法安全健康好喂食的食材有自制的鹦鹉奶粉或进口品牌的鹦鹉奶粉,里面包括细磨成粉状的谷类,再添加蛋白质、维生素或是消化酵素等,喂食幼雏可用幼鸟“专用汤匙”,其造型和一般汤匙不同,而是模仿亲鸟的鸟喙形状,使得幼鸟在进食流质时,易于进入口中而不会从四周流出。6、针筒喂食排净空气好针筒软管理喂食也是常见的方式,但是危险性相对较高。因为针筒在吸进液体时会有残留的空气储存于顶端,此时如果连空气一起注射入幼鸟的口中,针筒中残留顶端的空气会将幼鸟呛死,因此在使用针筒喂食前,一定要将其顶端的空气先排净,然后轻轻的推入幼鸟的口中,避免针筒刺伤幼鸟的舌头或是口腔。而软管喂食通常容易误插入幼鸟的气管内导致窒息而死。所以新手绝对不要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任意使用,否则很容易造成爱鸟死亡。7、断奶方法循序渐进好当健康状况良好的幼鸟接近2个半月大,出现索食意愿不强烈甚至拒食的情况时,可以准备糊状或是干料来训练教导幼鸟离乳。离乳期间可以采取少量多餐的方式给与幼鸟较稀的奶粉补充体力,过程必须循序渐进,不可立即断绝手喂鹦鹉奶粉而强迫其进食干料,否则幼鸟很可能会因为自己不会进食或是进食的份量不足而导致营养不良死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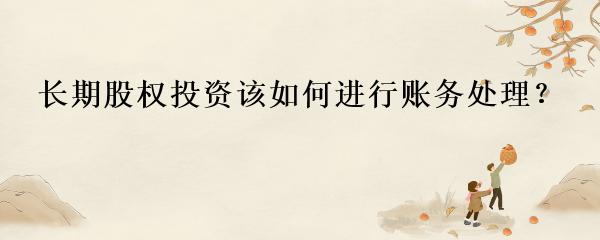 长期股权投资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长期股权投资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长期股权投资:是企业对其他企业进行的长期持有的,通过股权投资对被投资企业达到控制或者能对被投资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的,用以分散自身风险的,为企业自身带来经济利益的一种投资。(也就是企业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票)
长期股权投资计量又分为权益法和成本法,账务处理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入账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银行存款
二、收到股利时:
借:银行存款
贷:投资收益
三、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需要计提减值且不允许转回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长期股权投资资产减值准备
四、股利分发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投资收益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利息
五、处置时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即:处置收益=实际取得的价款-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借:银行存款等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贷:长期股权投资
(贷或借)投资收益
权益法下,处置该项投资时应当将原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部分按相应比例转入当期损益。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贷:投资收益
【注意】长期股权投资计算应该区分权益法还是成本法。
扩展文件; 《会计账务资料大全》
 如何投诉4S店
如何投诉4S店1、首推品牌厂家投诉,4S店是产品经销商,更注重于销售销量,而品牌厂家则是非常注重品牌建设和后期服务,对4S店有严格的资质审核和营运考核。通常情况下,只要给厂家投诉,4S店都会给出反应。厂家投诉电话在网上或产品手册中都可以找到。
2、拨打12315直接投诉4S店,只要投诉合理,都会配合解决。
3、媒体曝光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向当地主要媒体进行投诉,这个是4S店比较担心的,记者一旦上门进行曝光,门店信誉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品牌厂家也会有所牵连。所以找媒体投诉这个途径也是比较有效和快速的。
扩展资料:
发起投诉需要提交的信息:
包括车辆识别代码、注册日期、品牌车型、经销商工商注册全称、车架号、车牌号、所在地域、变速箱种类、投诉前是否发生过事故并报案等信息,便于投诉受理部门核实真实性。
切记不要冲动,不要闹事,就算是遇到了不公正的情况,内心十分气愤不平,也要先冷静下来,理智沟通问题,否则事情只会发展得更加严重,远离获得满意结果的初衷。
 小区业主怎么才能赶走目前的物业管理公司赶走一个物业公司首先要看小区是否有成立业主委员会(需要在政府备案登记的),有业委会就可以展开监督,不满意服务的,合同到期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其撤场并引进新的物业公司。如果合同还有比较长时间才到期,而且觉得服务已经严重不满意,可以按法规发起解聘程序:第一,召开业主大会,与会业主数需达到法定的比例,所决议的内容才能被法律认可;第二,进行投票是否解聘目前的物业公司,投票业主数需达到法定的比例,所决议的内容才能被法律认可;第三,投票赞成解聘的业主数需达到法定的比例,所决议的内容才能被法律认可;第四,投票结果由见证人签名确认,送相关职能部门备案登记。在此过程中最好邀请居委会,派出所,房管局,公证处等第三方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参与协调,以示投票的公正性和具备相应的法律意义。完成以后还有新旧物业公司的交接,这是重点。很多矛盾冲突就在此集中爆发。很多差的物业公司甚至无资质的物业公司所聘请的保安其实就是烂仔流氓,他们有相关的利益团体并不愿意撤场,或者不交接设备设施保养资料,或者打砸设备设施,或者新旧保安打架,都有可能发生。同时,他们还会提出要业主请还拖欠的物业管理费才进行交接等等。对拒绝撤场的物业公司,可以进行起诉等相关法律程序。那就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了。很多胜诉的也面临执行难等问题。如果连业主委员会都没有成立,那基本很难赶走。除非联合多数业主拒缴管理费、停车费,令它的运营产生严重困难。同时要提防其将停车场,泳池等业主共有公共设施经营剥离对外转让获利。更换新的物业公司也未必熟悉小区和附近地区的运营。同时大型楼盘的物业公司其实也承担了不少亏本经营来配合协助楼盘的销售。例如郊区楼盘进入市区的楼巴,入住率不高还要开放多个泳池,会所的健身设施月卡低于市场价等。一旦更换物业公司,新的物业公司无法和原有物业公司同样享受房产公司的补贴,这部分费用不可避免就分摊至管理费或享用者,或者降低服务标准以维持收支平衡。这些都是业主更换物业公司必须考虑的因素。综上所述,更换物业公司,其实就是平衡各方利益的一场谈判和博弈。
小区业主怎么才能赶走目前的物业管理公司赶走一个物业公司首先要看小区是否有成立业主委员会(需要在政府备案登记的),有业委会就可以展开监督,不满意服务的,合同到期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其撤场并引进新的物业公司。如果合同还有比较长时间才到期,而且觉得服务已经严重不满意,可以按法规发起解聘程序:第一,召开业主大会,与会业主数需达到法定的比例,所决议的内容才能被法律认可;第二,进行投票是否解聘目前的物业公司,投票业主数需达到法定的比例,所决议的内容才能被法律认可;第三,投票赞成解聘的业主数需达到法定的比例,所决议的内容才能被法律认可;第四,投票结果由见证人签名确认,送相关职能部门备案登记。在此过程中最好邀请居委会,派出所,房管局,公证处等第三方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参与协调,以示投票的公正性和具备相应的法律意义。完成以后还有新旧物业公司的交接,这是重点。很多矛盾冲突就在此集中爆发。很多差的物业公司甚至无资质的物业公司所聘请的保安其实就是烂仔流氓,他们有相关的利益团体并不愿意撤场,或者不交接设备设施保养资料,或者打砸设备设施,或者新旧保安打架,都有可能发生。同时,他们还会提出要业主请还拖欠的物业管理费才进行交接等等。对拒绝撤场的物业公司,可以进行起诉等相关法律程序。那就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了。很多胜诉的也面临执行难等问题。如果连业主委员会都没有成立,那基本很难赶走。除非联合多数业主拒缴管理费、停车费,令它的运营产生严重困难。同时要提防其将停车场,泳池等业主共有公共设施经营剥离对外转让获利。更换新的物业公司也未必熟悉小区和附近地区的运营。同时大型楼盘的物业公司其实也承担了不少亏本经营来配合协助楼盘的销售。例如郊区楼盘进入市区的楼巴,入住率不高还要开放多个泳池,会所的健身设施月卡低于市场价等。一旦更换物业公司,新的物业公司无法和原有物业公司同样享受房产公司的补贴,这部分费用不可避免就分摊至管理费或享用者,或者降低服务标准以维持收支平衡。这些都是业主更换物业公司必须考虑的因素。综上所述,更换物业公司,其实就是平衡各方利益的一场谈判和博弈。 一个人在两个地方有收入,个税如何申报
一个人在两个地方有收入,个税如何申报一个人在两个地方有收入,可以在取得所得后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个人所得税。多出所得可以选择并固定向其中一处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根据《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第二条 凡依据个人所得税法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一)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
(二)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
(三)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
(四)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
(五)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条 本办法第二条第一项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无论取得的各项所得是否已足额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均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于纳税年度终了后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本办法第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情形的纳税人,均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于取得所得后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本办法第二条第五项情形的纳税人,其纳税申报办法根据具体情形另行规定。
扩展资料: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第十一条 取得本办法第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所得的纳税人,纳税申报地点分别为:
(一)从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选择并固定向其中一处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二)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向中国境内户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在中国境内有户籍,但户籍所在地与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选择并固定向其中一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在中国境内没有户籍的,向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三)个体工商户向实际经营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暂时无法确定是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的,走什么程序
暂时无法确定是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的,走什么程序《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规定,对发现或者受理的案件暂时无法确定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的,可以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办理。在办理过程中,认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办理。
行政案件由县级公安机关及其公安派出所、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授权和管辖分工办理,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办理的除外。
扩展资料
行政争议一经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受理,即变为行政案件。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受理行政争议的前提是行政争议事实的存在和作为行政相对人一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提起。根据对行政争议进行处理的机关的不同,行政案件可分为以下两类:
1、行政机关自行处理的行政案件,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向该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法定机构提出申诉或控告,上述机关受理并予以解决的行政案件。
2、行政诉讼案件,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审判的行政案件。对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机关自行处理的行政案件,还可依法由人民法院予以审理和裁定。
 怎么可以查到自己的劳动合同有没有解除单位哪个部门负责保管劳动合同,可以去查一下。另外,劳动合同你应当有一份的,单位没有给你你可以去劳动局投诉。
怎么可以查到自己的劳动合同有没有解除单位哪个部门负责保管劳动合同,可以去查一下。另外,劳动合同你应当有一份的,单位没有给你你可以去劳动局投诉。 办理企业法人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什么资料?需要携带的主要材料有:户口薄、身份证原件,纳税记录,近期银行流水记录,村委会或街道办证明,结婚证等,港澳通行证,护照等。办理的流程:1、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开证明,居委会相关负责人知道具体的填写内容,然后盖章,签字;2、报片民警,签字盖章(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会协助帮你找到报片民警的姓名,联系方式的);3、到派出所最后签字、盖章。4、或者直接带个人身份证户口本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不过他们也许会卡流程。
办理企业法人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什么资料?需要携带的主要材料有:户口薄、身份证原件,纳税记录,近期银行流水记录,村委会或街道办证明,结婚证等,港澳通行证,护照等。办理的流程:1、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开证明,居委会相关负责人知道具体的填写内容,然后盖章,签字;2、报片民警,签字盖章(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会协助帮你找到报片民警的姓名,联系方式的);3、到派出所最后签字、盖章。4、或者直接带个人身份证户口本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不过他们也许会卡流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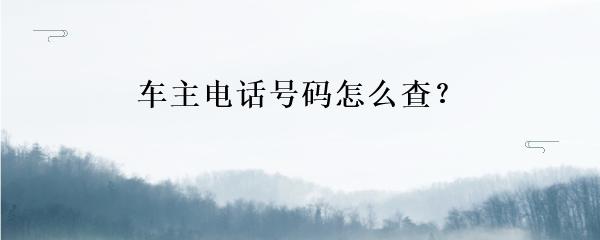 车主电话号码怎么查?
车主电话号码怎么查?看看车上有没有联系电话, 没有就打122交警或114电话。
1、拨通114,向话务员提供所需挪动机动车的牌号和地点,你的电话会直接转接到对方车主的手机上,但不会透露对方的号码。
2、拨通114后,客服人员称,已推出这项服务,但所挪车辆的车主需要在联通开通此项服务。“车主将自己的车牌号码与个人手机号在114登记后,就可以实现通过车牌找车主。”
联通信息导航业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其他用户只需拨通114,报出车牌号码,114便会将电话转接至车主,为更好地保护车主隐私,车主电话只转接,不报号。
3、由此可见,想通过114查询“挡道”司机电话是可以的,但享受这项服务是有前提的,需要车主到联通公司申请将手机号和车牌号捆绑,开通这项服务。如果没有登记,那114就帮不上忙了。
4、拨打122,询问话务员自己的车子被某某车牌号的车辆在哪个地点堵住了,能否提供挪车服务。话务员联系交警后,很快联系对方车主挪车,122作为交通事故报警电话具备这样的便民服务功能。
扩展资料:
一、122电话简介:
122报警服务台是我国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为受理群众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指挥调度警员处理各种报警、求助、同时受理群众对交通管理和交通民警执法问题的举报、投诉、查询等而设的部门。
该部门是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指挥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实行24小时值班。群众只要用电话拨打“122”即可免费接通122台电话。
二、114电话简介:
114是指为用户提供号码信息服务,传统业务有优先报号、语音报号、品牌查询、查询转接、临时报号、企业冠名、列名查询、排序报号、媒体延伸。
增值服务有116114法律顾问、教育导航、健康顾问、如意折扣、话匣子、就业顾问。
 怎样判断身份证是否消磁?
怎样判断身份证是否消磁?身份证并不存在消磁的概念,是身份证里的芯片损坏。身份证的芯片损坏是无法肉眼查看的,想确认是否损坏可以直接到当地派出所查询。
一代身份证没有磁,当然无法消。二代身份证不存在“消磁”和“补磁”的概念,身份证内装有芯片,芯片和交通卡芯片一样,都属于具有自动识别功能的RFID(电子标签)芯片的一种,芯片本身并没有磁性,和带磁条的银行卡完全属于两个类别,自然也不存在“被消磁”的可能。火车站购票机等系统如无法读取,说明芯片已损坏,若要获取完好的身份证,市民需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重新办理。
扩展资料
身份证的存放注意事项:
1、身份证只要不弯折扭曲它,避开潮湿和高温的环境,哪儿都能存放,也可以随身携带。
2、现在普遍使用的二代身份证,是芯片式身份证,不存在消磁的问题,在保存上与芯片式银行卡类似。
3、二代身份证的芯片,是无源存储器件,不必担心电磁干扰,可以放心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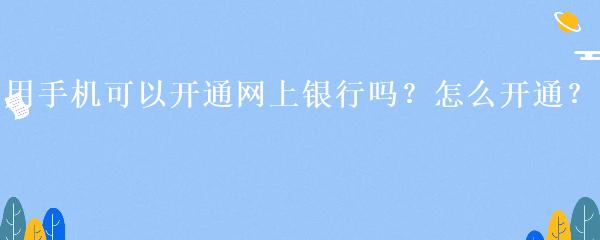 用手机可以开通网上银行吗?怎么开通?
用手机可以开通网上银行吗?怎么开通?1、首先要下载银行的APP,以农业银行为例,在百度搜索“农业银行”然后点击下载。
2、用账号跟密码登陆进去以后,点击客户服务,这时会出现下列表,此时点击电子银行渠道管理,这时会再次出现下列表,点击手机银行/申请手机银行。
3、这时候会出现让确认银行账号信息的页面,确定你的客户姓名及证件号码是否准确,确认无误以后,点击添加客户信息。
3、点完添加信息以后,会出现下图页面的内容,此时会出现绑定手机号,在后面输自己的手机号码,然后点击获取手机验证码,等收到验证码后输入进去,再输入手机银行渠道密码,再点击提交。
4、短信验证码已经发送到您的手机,请注意查收,60秒内没有收到请点击重新发送。
5、最后跳出下面的信息,如果确定无误以后,点击确认即开通了手机请确认您要提交的信息,注册手机银行号码,账户名称及卡的简称,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
 大学生如何模范履行依法服兵役义务?
大学生如何模范履行依法服兵役义务?法服兵役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公民最起码的要求;从国家层面讲,有国才有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要军队建设需要,作为青年都应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入伍,自觉投身于国防建设。
同时,也要用足用好各种征兵优惠政策,不仅要帮助适龄青年算好个人“政治账”“经济账”“前途账”“素质账”和“阅历账”,更要算好国家“发展账”“安全账”,引导广大适龄青年把个人理想和国家需要有机结合起来,激发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爱国热情。
扩展资料:
坚持正面宣传引导是征兵宣传发动的主流,同时也加大对拒服兵役、逃避兵役青年处罚的宣传,强化兵役法规的强制性、权威性,营造依法服兵役的社会氛围。
一方面要依据《兵役法》有关对拒服、逃避兵役处罚的条款,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处罚标准和条件等,制定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处罚规定;另一方面要加大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的宣传,在各种公共场合对拒服、逃避兵役者进行曝光,公示对其处罚措施。
同时要大力开展依法服兵役的役前教育,使应征青年和家长明白逃避服兵役将会受到法律的处罚,个人成长进步会留污点,真正使“依法服兵役,参军尽义务”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自觉行为。
 如何提升把握大局和服务大局的能力1、首先提高眼界,不要局限到具体内容上边去2、掌握同行或者同类型的新闻动态,政府政策动向。3、多思维多角度考虑4、增强战略性思维的培训5、多接触高端环境和高端人群6、多看兵法和商业战类的书籍。
如何提升把握大局和服务大局的能力1、首先提高眼界,不要局限到具体内容上边去2、掌握同行或者同类型的新闻动态,政府政策动向。3、多思维多角度考虑4、增强战略性思维的培训5、多接触高端环境和高端人群6、多看兵法和商业战类的书籍。 以公司名义起诉个人都需要什么资料
以公司名义起诉个人都需要什么资料起诉须提交的材料
1、起诉状
(1)原告与被告的基本信息;
(2)诉讼请求;
(3)事实与理由。
2、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1)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记载其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住所、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的材料如身份证、户口簿、居住证明、护照、港澳台胞回乡证;
(2)当事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注册登记证书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书。
3、原告提交起诉状时应当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4、原告提交起诉状时应当一并提交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5、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的应当一并提交委托授权材料。
扩展资料:
民事诉讼一审的程序
1、起诉,即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立案庭递交诉状。
2、立案审查
符合立案条件,通知当事人7日内交诉讼费,交费后予以立案;不符合立案条件,裁定不予受理。
如果对裁定驳回起诉不服,10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受理后,法院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15日内进行答辩,通知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可根据当事人申请,做出财产保全裁定,并立即开始执行
3、排期开庭
提前3日通知当事人开庭时间、地点、承办人;公开审理的案件提前3日进行公告。
4、开庭审理
宣布开庭,核对当事人身份,宣布合议庭成员,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询问是否申请回避。
法庭调查:当事人陈述案件事实。
举证质证: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出示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双方当事人就证据材料发表意见。
法庭辩论:各方当事人就有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辩驳和论证。
法庭调解:在法庭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协议解决纠纷。
如果达成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签收后生效,当事人履行调解书内容或申请执行;未达成调解协议,合议庭合议作出裁决(宣判)。
5、宣判
同意判决,当事人自动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或向我院告诉庭提出执行申请;不同意裁判,需要分情形区分对待:
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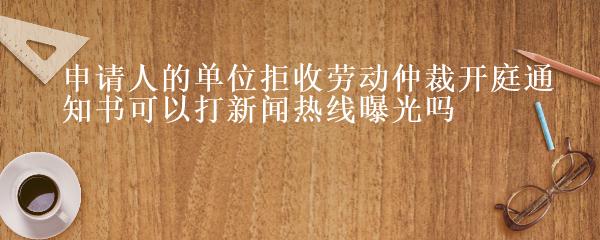 申请人的单位拒收劳动仲裁开庭通知书可以打新闻热线曝光吗申请人的单位拒收劳动仲裁开庭通知书可以打新闻热线曝光,但是如果走到仲裁程序了,就没有必要打新闻媒体曝光;一、如果单位拒收劳动仲裁开庭通知书仲裁委可以通过打公告的形式进行送达,这个不需要劳动者担心;二、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在指定的期限内到庭开庭,将会面临败诉的风险;
申请人的单位拒收劳动仲裁开庭通知书可以打新闻热线曝光吗申请人的单位拒收劳动仲裁开庭通知书可以打新闻热线曝光,但是如果走到仲裁程序了,就没有必要打新闻媒体曝光;一、如果单位拒收劳动仲裁开庭通知书仲裁委可以通过打公告的形式进行送达,这个不需要劳动者担心;二、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在指定的期限内到庭开庭,将会面临败诉的风险; 事故逃逸司机要怎么处罚?
事故逃逸司机要怎么处罚?《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试行)》第十三条规定:对肇事逃逸的,对驾驶人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15日以下拘留,记12分;交通肇事后逃逸,并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致一人死亡或三人重伤以上,负主要或全部责任)的,将被判处3-7年有期徒刑。如果因逃逸致使人死亡的,将受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处罚。
扩展资料:
1.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谓“交通肇事后逃逸”,《解释》第3条规定,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这里要注意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认定,首先,交通肇事逃逸的前提条件是“为逃避法律追究”,其次,交通肇事逃逸并没有时间和场所的限定,不应仅理解为“逃离事故现场”,对于肇事后未逃离(或未能逃离)事故现场,而是在将伤者送至医院后或者等待交通管理部门处理的时候逃跑的,也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所谓“其他特别恶劣情节”,《解释》第4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1)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六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
2、因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何能把面试的钱要回来?面试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如果让你交费或者叫培训费都是不合理的,建议也不要给,更不要去这样的公司上班;如果你已经交钱了,对方是否给你开具发票或者收据,或者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对方收取费用,可以找相关部门把钱要回,如果什么都没有很难要回。
如何能把面试的钱要回来?面试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如果让你交费或者叫培训费都是不合理的,建议也不要给,更不要去这样的公司上班;如果你已经交钱了,对方是否给你开具发票或者收据,或者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对方收取费用,可以找相关部门把钱要回,如果什么都没有很难要回。 什么是信息?信息有哪些特点
什么是信息?信息有哪些特点信息指音讯消息通讯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泛指人类社会传播的一切内容。
信息的特点:
①依附性:信息必须依附一定的媒体介质表现出来。
②价值性:信息能够满足人们某些方面的需要。
③时效性:信息会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
④共享性:一个信息可以由多分进行分享。
⑤传递性:(信息的传递性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扩展资料:
信息的传递
远古时代
1、口耳相传或借助器物。
2、信息传递速度慢、不精确古代。
3、靠驿差长途跋涉。
4、信息传递速度慢、信息形式单一。
近代
1、依靠交通工具的邮政系统。
2、信息传递速度相对快一些、距离远相对就慢、且费用高。
现代
1、电报、电话。
2、速度快、信息单一文字。
当代
1、计算机网络。
2、传递的信息量大、信息多样化,传递速度极快、不受地域阻碍。
 失业金是什么?失业金是失业保险金,是指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支付给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是对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失去工资收入的一种临时补偿。失业保险金目的是为了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失业保险金依法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失业金是什么?失业金是失业保险金,是指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支付给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是对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失去工资收入的一种临时补偿。失业保险金目的是为了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失业保险金依法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投资公司主要是做什么的?金融投资公司是一个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出资额为限依法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实现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投资公司,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金融中介机构,将个人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投资于众多证券或其他资产之中。
投资公司主要是做什么的?金融投资公司是一个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出资额为限依法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实现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投资公司,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金融中介机构,将个人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投资于众多证券或其他资产之中。 省高院审判管理处处长是什么行政级别省高院虽然主管领导按副省享受级别待遇,实际上它还是正厅级机构。因此,省高院审判管理处处长一般都是正处级公务员,如果高配的话,也可能是副厅级公务员。
省高院审判管理处处长是什么行政级别省高院虽然主管领导按副省享受级别待遇,实际上它还是正厅级机构。因此,省高院审判管理处处长一般都是正处级公务员,如果高配的话,也可能是副厅级公务员。 什么是恶意订购恶意订购,就是买方在主观上存在恶意行为,实际上并没有订购商品的意图。恶意订购,一般需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正当竞争等,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需要看情节定。
什么是恶意订购恶意订购,就是买方在主观上存在恶意行为,实际上并没有订购商品的意图。恶意订购,一般需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正当竞争等,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需要看情节定。 在蛋糕店打工需要什么条件?如果是店员或者学徒的话不需要什么条件,只要对这份工作肯干就可以了。如果是要应聘糕点师的话就需要有一定的能力了,建议最好还是从学徒开始,毕竟一口吃不成胖子。当然如果已经有这方面的相关经验的话也可以直接去做糕点师傅的说,祝你成功。
在蛋糕店打工需要什么条件?如果是店员或者学徒的话不需要什么条件,只要对这份工作肯干就可以了。如果是要应聘糕点师的话就需要有一定的能力了,建议最好还是从学徒开始,毕竟一口吃不成胖子。当然如果已经有这方面的相关经验的话也可以直接去做糕点师傅的说,祝你成功。 参加联通新入网充值返话费活动送的话费什么时候返还?再得的话费按月返还,每月返还10元,首次返还话费将于充值后48小时内到账;次月起剩余返还话费将于每月月初4个工作日内到账,返还话费到账将以短信形式通知,请您留意短信提醒。
参加联通新入网充值返话费活动送的话费什么时候返还?再得的话费按月返还,每月返还10元,首次返还话费将于充值后48小时内到账;次月起剩余返还话费将于每月月初4个工作日内到账,返还话费到账将以短信形式通知,请您留意短信提醒。 刑事拘留通知书里面为什么没写拘留多长时间?刑事拘留最长时间是30天,检察院7天的批捕时间,批捕后一般案件有两个月的侦查羁押期限,这些都是法定的时限,所以刑事拘留通知书上面不会有时间。
刑事拘留通知书里面为什么没写拘留多长时间?刑事拘留最长时间是30天,检察院7天的批捕时间,批捕后一般案件有两个月的侦查羁押期限,这些都是法定的时限,所以刑事拘留通知书上面不会有时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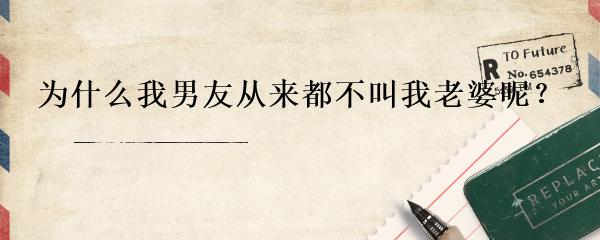 为什么我男友从来都不叫我老婆呢?不叫了,可能有多种原因吧,不叫因为需要双方冷静下来思考,你是不是他唯一的选择。如果在一起老是吵架,那以后在一起生活会有更多的问题点,给自己和他一点时间去思考吧,如果总是因一些小事而吵确实没必要!相爱就要彼此珍惜对方,且行且珍惜!
为什么我男友从来都不叫我老婆呢?不叫了,可能有多种原因吧,不叫因为需要双方冷静下来思考,你是不是他唯一的选择。如果在一起老是吵架,那以后在一起生活会有更多的问题点,给自己和他一点时间去思考吧,如果总是因一些小事而吵确实没必要!相爱就要彼此珍惜对方,且行且珍惜!




 微信
微信
 微博
微博
 QQ空间
QQ空间
 复制网址
复制网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