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作用范围的界限不清,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权力在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划分上存在问题,因而梳理基本的权力结构关系对于理解和界定行政违法和犯罪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行政性犯罪的认定,应特别考虑行政违法性的存在,而从权力运作的角度看,即表现为特定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而这一权力行使对于相应案件的犯罪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行政违法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功能不同,其反映的是权力运作关系的不同,因而当同一行为既是行政违法又构成犯罪的情形下,行为人承担两种不同的责任,并不存在责任的充分评价问题。行政违法和以违反行政性法律、法规为前提的所谓行政犯罪之区分,行政犯罪之刑法解释及认定,以及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之衔接问题,在今日之法治语境下进行研究,不单纯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更主要地表现为一个实践问题。而对这类问题研究之切入,在规范层面去探索进路,是当前之主要研究视域,即所谓以行政刑法或者行政犯为基本范畴进行所谓之本体研究,而又以比较法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德国、日本法律实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情形。这种视域和方法,不可谓不当,但是对于中国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实质上是行政权与司法权)之关系问题,在这种研究框架下是难以澄清的,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也如摆在花坛里的盆花,虽然鲜艳、茂盛,却和下面的土壤没有直接关系。本文试图将研究视角作必要的转换,从权力分配与重叠的角度进行基础性的现象分析,进而基于现象观察,抽象出问题脉络,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路。上述问题的实质在于,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的划分、衔接以及因为权力作用范围重叠而形成冲突和解决,因而本文的切入点就从权力的分配开始,并于权力的实现结束。一、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纠葛的宪政视角权力分配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其次才是法律问题。国家基本权力在不同国家机构中的划分也是如此。公权力在国家层面作不同的组织架构的分配,并以宪法予以确认,这是当今宪政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之一。在我国虽然并不提倡“三权分立”的权力分配、实施及相互制约框架,但是基本权力在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划分、实施及相互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在宪法上仍十分清晰地被表现出来。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在我国,司法权的功能、独立性和强度都受到行政权(有时还来自于立法权)的挤压,对司法权性质的定位也与一些法治发达国家不尽一致。行政权在社会规制方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司法权应发挥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行政处罚权的作用宽广和行政强制教育措施权的存在。[1]在一定历史时期,国家在社会规制方面偏重行政权无可厚非,但是,当法治作为社会核心价值提出并着手建设时,以宪政维度来重新分配并平衡各种国家权力时,则对行政权应作重新的审视。司法权本身具有内敛的性质,其运行完全依照既有法律来运作。从目前的司法权运作看,虽然存在一定的自我创设权力的事例,但是总体上司法权施加的范围是比较清晰的。不过,当这种权力与行政权重叠的时候,就存在模糊的状态,这并不表明司法权进入到了行政权作用的空间,而是行政权作用的界限是模糊的,并有意、无意地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司法权应作用的空间。刑罚权,作为一种实体性、终局性的权力,其性质应归属于司法权,从国家权力分配而言,是由法院来行使的,集中体现为定罪和量刑的权力。当然,如果从广义上讲,制刑权(立法机关行使)、动刑权(侦查机关行使)、求刑权(检察机关行使)和行刑权(刑罚执行机关行使),也可以视为刑罚权的组成部分。不过,真正具有确定案件性质和决定某人具有刑事责任以及是否给予刑罚处罚的,只能由典型意义的司法机关即法院来完成。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权的一种形式,根据行政法律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行使,这种权力也是实体性且具有终局性的权力。所谓行政权替代了司法权的行使,以刑事法为本位,集中表现为行政处罚权替代了刑罚权的行使。具体而言,就是本应由刑罚权(狭义的)来处理的案件,却由行政处罚权进行终局处理。这一问题实际又包含了两个层次:(1)在宪政框架下进行权力分配,将本应由刑罚权解决的问题,交由行政处罚权来解决,比如劳动教养权、部分剥夺人的自由和财产的权力(行政拘留、行政罚款)在目前体制下都被视为行政权的范畴。(2)在权力现实运作层面,行政处罚权的行使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事实上替代了司法权应作用的事项。第一个层次是非常基础而复杂的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宪法问题;第二个层次则可以从操作层面上探讨,当然这个层次的探讨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或者说,导致后一层次问题更深刻的原因在于第一个层次。
 野荷的香馥
2022-07-13
野荷的香馥
2022-07-13  办塑料颗粒厂需要什么手续?
办塑料颗粒厂需要什么手续?办理的基本步骤如下:1、首先到工商部门名称核准.有些行业需要相关部门的预批准.2、注册资金验资 .3、找主管部门.工业的找经贸局或经贸局,农业找农业局等等之类,有一个批准的文件.4、按工商部门的要求准备好材料,上交,一般15天之内可以拿到营业执照.5、到税务部门领取税务登记证.
《个体户营业执照》的材料如下:
1.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证件相片.
3.工厂的房产证明文件复印件(房产证或者土地证啥的),如果是租的还需要租赁合同原件和复印件.
生产工艺
1、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颗粒保温砖
2、泡沫塑料颗粒混合轻量土及生产方法
3、生产可倾注的球弓形塑料填充颗粒的方法
4、塑料颗粒预热器
5、用于塑料颗粒的连续晶方法和装置
6、废絮制造CA塑料颗粒的方法及其专用拉丝机
7、塑料添加剂的低粉尘颗粒
8、用于使塑料、漆和建筑材料着色的无机颜料颗粒和其生产方法
9、将颗粒物料或土壤沉积在展开于填埋场表面或其它位置上面的塑料薄膜上的设备
10、塑料颗粒熔结滤芯
11、用于切削塑料膜颗粒刀具的制作方法
12、塑料加工用颗粒化助剂的制备方法
13、塑料管颗粒座具垫
14、内胆式塑料管颗粒座具垫
15、用泡沫塑料颗粒作夹层填充料的服装
16、生活垃圾塑料颗粒浮选装置
17、颗粒塑料除湿干燥系统
18、制备有色塑料或有色聚合颗粒的方法
19、用于生产可溶于塑料的着色剂的颗粒制剂的方法
20、由塑料熔体制备球形颗粒
 上海驾驶证到期换证需要什么手续?驾驶证到期换证,按如下流程办理:1、准备2张一寸照片,体检合格证明,其中的一张照片贴在体检表的右上方,另一张留着换新证用。2、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到办证大厅,填写换证申请表,然后把证件和体检合格表、换证申请表交给工作人员,缴纳10元的工本费,就等着拿新证了。3、换证前要先查一下有没有没处理的违法记录,有的话,要先处理掉,否则不给办理换证的。4、换证可以提前90天进行,合理安排时间,不要过期,过期没换证的,交警查到你,要罚款50元,不扣分。5、换证准备的照片和体检证明最好在交警队办证大厅直接办理,两项各收费10元,否则自带的怕不合格,还要重新拍照、体检耽误时间。6、换证是当场就办理完毕的,但一些大城市需要几天的时间,但最多不能超过15天,必须办理完毕,然后通知你去取新驾照。
上海驾驶证到期换证需要什么手续?驾驶证到期换证,按如下流程办理:1、准备2张一寸照片,体检合格证明,其中的一张照片贴在体检表的右上方,另一张留着换新证用。2、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到办证大厅,填写换证申请表,然后把证件和体检合格表、换证申请表交给工作人员,缴纳10元的工本费,就等着拿新证了。3、换证前要先查一下有没有没处理的违法记录,有的话,要先处理掉,否则不给办理换证的。4、换证可以提前90天进行,合理安排时间,不要过期,过期没换证的,交警查到你,要罚款50元,不扣分。5、换证准备的照片和体检证明最好在交警队办证大厅直接办理,两项各收费10元,否则自带的怕不合格,还要重新拍照、体检耽误时间。6、换证是当场就办理完毕的,但一些大城市需要几天的时间,但最多不能超过15天,必须办理完毕,然后通知你去取新驾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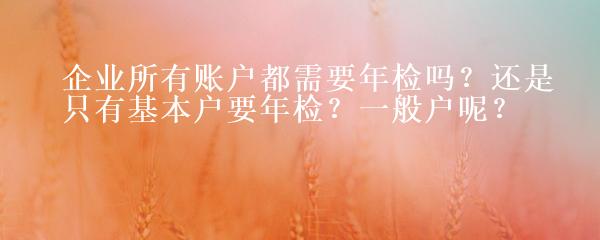 企业所有账户都需要年检吗?还是只有基本户要年检?一般户呢?
企业所有账户都需要年检吗?还是只有基本户要年检?一般户呢?不是的,基本户要年检,一般户不需要年检。
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第六十一条
银行应明确专人负责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使用和撤销的审查和管理,负责对存款人开户申请资料的审查,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及时报送存款人开销户信息资料,建立健全开销户登记制度,建立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档案,按会计档案进行管理。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档案的保管期限为银行结算账户撤销后10年。
第六十二条
银行应对已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实行年检制度,检查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的合规性,核实开户资料的真实性;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应予以撤销。对经核实的各类银行结算账户的资料变动情况,应及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
银行应对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的情况进行监督,对存款人的可疑支付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程序及时报告。
扩展资料:
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基本存款账户是存款人因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需要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下列存款人,可以申请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一)企业法人。
(二)非法人企业。
(三)机关、事业单位。
(四)团级(含)以上军队、武警部队及分散执勤的支(分)队。
(五)社会团体。
(六)民办非企业组织。
(七)异地常设机构。
(八)外国驻华机构。
(九)个体工商户。
(十)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
(十一)单位设立的独立核算的附属机构。
(十二)其他组织。
第十二条
一般存款账户是存款人因借款或其他结算需要,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以外的银行营业机构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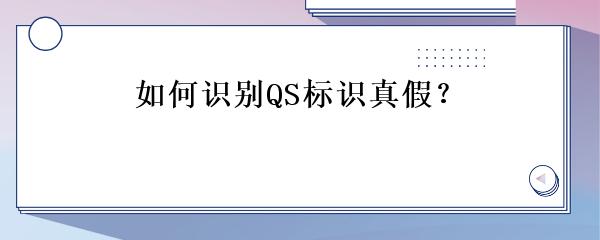 如何识别QS标识真假?1、识别QS标识真假:QS号码有一定的规律性,消费者可凭数字号码来识别真假。所有QS号码均由12位数字组成,前4位为认证受理机关的编号,一般是指企业所在地行政区划的代码,中间4位数字为产品类别代号,后4位数字为该产品通过QS认证的顺序号。有条件的消费者可上国家质监局网站查询,将QS码输入,看是否和企业产品相对应,可以立即辨别真假。2、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标志由‘企业产品生产许可’拼音Qiyechanpin Shengchanxuke的缩写‘QS’和‘生产许可’中文字样组成。标志主色调为蓝色,字母‘Q’与‘生产许可’四个中文字样为蓝色,字母‘S’为白色。标志的式样、尺寸及颜色要求见附件6。第一:QS不是认证标志,是生产许可证标志。第二:实行生产许可证的不是只有食品,而且包括其他。
如何识别QS标识真假?1、识别QS标识真假:QS号码有一定的规律性,消费者可凭数字号码来识别真假。所有QS号码均由12位数字组成,前4位为认证受理机关的编号,一般是指企业所在地行政区划的代码,中间4位数字为产品类别代号,后4位数字为该产品通过QS认证的顺序号。有条件的消费者可上国家质监局网站查询,将QS码输入,看是否和企业产品相对应,可以立即辨别真假。2、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标志由‘企业产品生产许可’拼音Qiyechanpin Shengchanxuke的缩写‘QS’和‘生产许可’中文字样组成。标志主色调为蓝色,字母‘Q’与‘生产许可’四个中文字样为蓝色,字母‘S’为白色。标志的式样、尺寸及颜色要求见附件6。第一:QS不是认证标志,是生产许可证标志。第二:实行生产许可证的不是只有食品,而且包括其他。 公司基本账户之间转账手续费是怎么收的?公司账户汇款:1万元以下(含1万元)每笔收费5元;1万元以上至10万元每笔收费10元;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每笔收取15元;5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每笔收取20元;100万元以上每笔按汇划金额的万分之零点二收取,最高不超过200元。另外,再加收0.5元手续费。私人汇款:中行:交易金额的1%;最低1元,最高50元工行:交易金额的1%;最低2元,最高100。基本账户主要是用来存钱、取钱、转账的公司账户,每个公司只能有一个基本账户,此账户为公司正常使用账户,可以随时存入或取出资金,取出资金的方式要通过公司现金支票或转账支票支取。
公司基本账户之间转账手续费是怎么收的?公司账户汇款:1万元以下(含1万元)每笔收费5元;1万元以上至10万元每笔收费10元;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每笔收取15元;5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每笔收取20元;100万元以上每笔按汇划金额的万分之零点二收取,最高不超过200元。另外,再加收0.5元手续费。私人汇款:中行:交易金额的1%;最低1元,最高50元工行:交易金额的1%;最低2元,最高100。基本账户主要是用来存钱、取钱、转账的公司账户,每个公司只能有一个基本账户,此账户为公司正常使用账户,可以随时存入或取出资金,取出资金的方式要通过公司现金支票或转账支票支取。 暂住证注销需要什么证件?
暂住证注销需要什么证件?暂住证注销需要以下材料:
1、本人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并提交详细信息,包括暂住事由、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服务处所、携带儿童、联系方式等等信息;
2、居住在居民家中的,提交户主的身份证或户口簿的复印件;
3、居住在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或者矿山、工地、林场、船舶等场所的,应当提交单位或者雇主开具的居住证明。
暂住证要到原来办理这张《暂住证》的机构注销。注销《暂住证》须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或其它有效证明。具体问题请咨询当地公安派出所、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或社区居委会。
暂住证有有效期的,过期自然作废。如果暂住已经过期,就不再需要办理相关的注销手续,如果还在有效期限内,则需要办理注销手续后。
扩展资料:
暂住证注销流程:
一、提前终止的申请报告(一式两份)。
注:
1、抬头:XX公司;
2、正文内要写明注销的具体原因及内容;
3、落款:企业名称、日期并加盖公章。
二、经各董事签名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董事会决议。 注:须有时间、地点,并由全体董事同意并亲笔签名。
三、各方加盖公司公章确认或公司董事长签名确认的董事会成员名单。 注:落款须含日期并加盖公章。
四、注明时间、地点的提前终止经营的协议(原件,独资企业不需要)。
五、已年检的企业批准证书正本及副本二原件、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六、经中国法定验证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近年审计报告(如皆为复印件,须加盖企业骑缝章)。
七、资产负债表、财产清单、债权人名单、债务人名单。
八、债权、债务处置情况说。
 工伤出院后复查费用怎么报销
工伤出院后复查费用怎么报销如果参加工伤保险,可以凭借正规的医疗发票到社保部门报销;如果没有参保,则到用人单位报销。
法律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职工治疗工伤应当在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就医,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
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部门规定。
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以及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报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通、食宿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基金支付的具体标准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规定。
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引发的疾病,不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处理。
工伤职工到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进行工伤康复的费用,符合规定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 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
(一)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
(二)住院伙食补助费;
(三)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
(四)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
(五)生活不能自理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生活护理费;
(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至四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
(七)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八)因工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死亡补助金;
(九)劳动能力鉴定费。
扩展资料:
工伤期间待遇:
一、医疗费:
要求: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
用人单位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不是必须到签有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治疗。
二、伙食补助:
标准:基金支付的具体标准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规定。
要求:住院期间。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0条第4款。
三、交通食宿费:
标准:基金支付的具体标准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规定。
要求:医疗机构出具诊断证明,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0条第4款。
四、康复治疗费: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0条第6款。
备注:依地方规定,康复治疗需经办机构组织专家评定。
五、辅助器具费:
标准:各省、直辖市工伤辅助器具限额标准。
要求:因日常生活或者就业需要,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安装假肢、矫形器、假眼、假牙和配置轮椅等辅助器具。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0条。
六、停工留薪:
标准: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
要求: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12个月。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3条。
备注:停工留薪期根据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和各地的停工留薪期分类目录确定,但确定的部门和程序,依地方规定。
七、护理费:
标准:(1)停工留薪期内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2)评定伤残后需要护理的,完全生活不能自理,按统筹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大部分生活不能自理,统筹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0%;部分生活不能自理,统筹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 ;
要求:生活护理费需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工伤职工按月享受。
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1条第3款、第32条。
 如何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完善环境法律体系一是加强调研,建立和完善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环境法律法规。要全面形成水、气、声、固废、辐射放射、环境影响评价等一系列环境法律体系;二是及时修订和完善现行环境法律法规。对不适应经济发展和人们生存需要的环境法律法规,要根据环境保护的新要求适时修订和完善,使之更能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具有可操作性;三是要将污染减排、环保实绩考核、生态补偿和环境税等纳入环境法律规范范畴,将其形成法律制度,使环境执法更加有力;四是明确环境法律责任,特别要明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要通过法律使政府及部门官员重视和加强环境保护,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如何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完善环境法律体系一是加强调研,建立和完善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环境法律法规。要全面形成水、气、声、固废、辐射放射、环境影响评价等一系列环境法律体系;二是及时修订和完善现行环境法律法规。对不适应经济发展和人们生存需要的环境法律法规,要根据环境保护的新要求适时修订和完善,使之更能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具有可操作性;三是要将污染减排、环保实绩考核、生态补偿和环境税等纳入环境法律规范范畴,将其形成法律制度,使环境执法更加有力;四是明确环境法律责任,特别要明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要通过法律使政府及部门官员重视和加强环境保护,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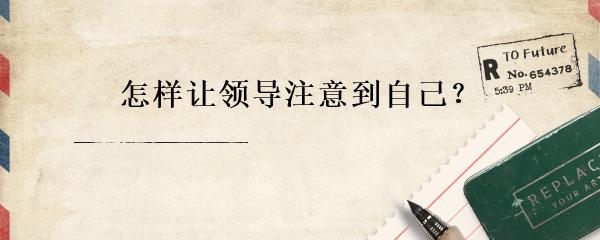 怎样让领导注意到自己?
怎样让领导注意到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再众多的职工当中更加出众,再或者是成为职场上的精英。这样,只有当你变得更加强大的时候,领导才会去关注你才会知道你。
当你做事麻利大方,而且做的井井有条并且出错率特别的低,那么你的业绩就会是职工当中最好最高的,而且领导最关注的就是那些业绩特别好的,而且特别会办事的人,你自然会成为老板的意中人之一!
而且一定要外貌精神,阳光向上,积极奋进,看起来特别的给人带来希望的感觉,然后如果是女生的话,一定要学会打扮自己,给自己化化妆,让自己的衣着得体一点,这样才能显得特别落落大方。如果是男生的话,就一定要学会察言观色,摸清老板的个人喜好,只有你才,能走进领导的内心世界,才能够符合老板的心意。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你足够了解一个人的时候,那一个人必定与你同行。
要对自己苛刻一点,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要积极奋进,时刻保持一副阳光向上的面貌,让人看起来就特别的拥有精神的感觉,等你有精神了,你给别人表现出来的活力才能感染其他人,领导也不例外,领导一定会被你身上的那种特别的气质所吸引,这时你就被领导成功的注意到了。
其实被领导注意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如果你用心做了,也不是一件难事。比如说大早上起来给领导泡一些咖啡,让他提提神,中午的时候帮领导买一些饭后甜点,比如说水果和点心,在晚上的时候可以陪老板喝一杯酒,聊聊心里话。和老板交流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一个领导是高高在上的,一定是特别的孤独,如果这时有人去当他的知己,当他倾诉的对象,他一定会特别开心,一定会记住你。
 大学毕业生怎样落户口?
大学毕业生怎样落户口?将户口转为原来户籍所在地即可。
落户口的具体流程如下:
一、户口在学校的毕业生,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将户口由学校迁移到工作单位所在地。工作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凭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签发的《就业报到证》和用人单位主管部门的接收证明及学校所在地公安机关签发的《户口迁移证》办理入户手续。二、户口不在学校的毕业生,落实工作单位的,凭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签发的《就业报到证》和用人单位主管部门的接收证明,就可将户口由原籍直接迁至工作单位所在地。户口迁出地公安机关凭《就业报到证》和用人单位主管部门的接收证明,直接办理《户口迁移证》,工作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不需发《准予迁入证明》。三、户口在学校的毕业生,要求将户口迁回原籍的,公安机关凭毕业生本人的毕业证和《户口迁移证》办理恢复户口手续。四、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离开学校时,还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可暂缓2年就业。暂缓就业毕业生的户口可继续保留在学校2年。毕业生在暂缓就业期间落实工作单位的,公安机关凭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签发的《就业报到证》和用人单位主管部门的接收证明,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暂缓就业毕业生,在暂缓期满后仍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可按照有关规定将户口迁回原户口迁出地。五、户口在学校的原农业户口性质毕业生,要求将户口迁回原籍,并要求恢复农业户口性质的,可予办理。为妥善处理好“非转农”后出现的问题,事先应征求申请“农业户口”所在地的乡镇或村委会意见。六、入学时未将户口办理“农转非”手续的毕业生,落实工作单位后,在办理户口迁出时,户口迁出地公安机关在为其办理“农转非”手续后,以“非农业”户口性质迁出。七、户口在学校的本省生源毕业生,未落实工作,要求将户口迁回原籍,其父母户口已迁移到本省其他地区的,可直接将户口迁至其父母户口所在地;如果父母一方还在原籍居住的,该毕业生的户口仍应迁回原籍。八、已领取《迁移证》将户口迁回原籍的毕业生,因故一直未办理落户手续,迁入地公安机关问明情况后,凭原《迁移证》恢复户口;已领取《迁移证》将户口迁往异地,因故一直未办理落户手续的,按有关管理规定办理。
不管哪种情况,都需要带着身份证、户口本、户口迁移证、就业报到证或派遣证等材料,办理相应的户口迁移手续。
 建筑业发票中个人所得税怎么列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建筑安装业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6]127号)第十一条规定,在异地从事建筑安装业工程作业的单位,应在工程作业所在地扣缴个人所得税。这个个人所得税是根据开具发票时的发票金额由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收取,一般为开票金额的千分之八或百分之一,是由建筑安装企业承担的,具体的会计处理分为两种情况。一、个人所得税不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会计处理顾名思义,个人所得税是由个人承担的税种,一般情况下个人才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单位只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人,单位缴纳的所得税是企业所得税。只有建筑安装企业在异地从事工程作业才会涉及到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既然是个人所得税,按理是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目前的税法文件也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因此很多税务机关都不允许在税前扣除。这种情况下的会计处理举例如下:例1.苏州建筑工程公司在无锡有一建筑工程,合同金额为300万元,实际结算金额也是300万元,工程完工,在无锡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开具建筑业发票300万元,缴纳了9万元的营业税、0.63万元的城市维护建设税、0.27万元的教育费附加、0.18万元的地方教育附加,2.4万元的个人所得税、0.09万元的印花税。根据300万元的建筑业发票。借:应收账款 3000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3000000根据缴纳的税费单据。借: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90000借: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6300借: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2700借:应交税费—应交地方教育附加 1800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4000借:管理费用—印花税 900贷:库存现金125700由于个人所得税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而企业又必须承担的,这笔个人所得税只能在企业的留存收益中列支,减少留存收益。同时根据已缴纳的税费计提并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00800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90000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6300贷: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2700贷:应交税费—应交地方教育附加 1800二、个人所得税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会计处理由于税法没有明确规定单位承担的个人所得税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有些地方的税务机关对此是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这种情况下的会计处理举例如下:例2.广州建筑工程公司在珠海有一建筑工程,合同金额为300万,实际结算金额也是300万,工程完工,在珠海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开具建筑业发票300万元,缴纳了9万元的营业税、0.63万元的城市维护建设税、0.27万元的教育费附加、0.18万元的地方教育附加,2.4万元的个人所得税、0.09万元的印花税。根据缴纳的税费单据。借: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90000借: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6300借: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2700借:应交税费—应交地方教育附加 1800借:管理费用—税金 24900(2.4万元+0.09万元)贷:库存现金125700贷:其他会计分录同例1.,这里不再叙述。
建筑业发票中个人所得税怎么列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建筑安装业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6]127号)第十一条规定,在异地从事建筑安装业工程作业的单位,应在工程作业所在地扣缴个人所得税。这个个人所得税是根据开具发票时的发票金额由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收取,一般为开票金额的千分之八或百分之一,是由建筑安装企业承担的,具体的会计处理分为两种情况。一、个人所得税不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会计处理顾名思义,个人所得税是由个人承担的税种,一般情况下个人才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单位只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人,单位缴纳的所得税是企业所得税。只有建筑安装企业在异地从事工程作业才会涉及到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既然是个人所得税,按理是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目前的税法文件也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因此很多税务机关都不允许在税前扣除。这种情况下的会计处理举例如下:例1.苏州建筑工程公司在无锡有一建筑工程,合同金额为300万元,实际结算金额也是300万元,工程完工,在无锡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开具建筑业发票300万元,缴纳了9万元的营业税、0.63万元的城市维护建设税、0.27万元的教育费附加、0.18万元的地方教育附加,2.4万元的个人所得税、0.09万元的印花税。根据300万元的建筑业发票。借:应收账款 3000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3000000根据缴纳的税费单据。借: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90000借: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6300借: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2700借:应交税费—应交地方教育附加 1800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4000借:管理费用—印花税 900贷:库存现金125700由于个人所得税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而企业又必须承担的,这笔个人所得税只能在企业的留存收益中列支,减少留存收益。同时根据已缴纳的税费计提并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00800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90000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6300贷: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2700贷:应交税费—应交地方教育附加 1800二、个人所得税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会计处理由于税法没有明确规定单位承担的个人所得税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有些地方的税务机关对此是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这种情况下的会计处理举例如下:例2.广州建筑工程公司在珠海有一建筑工程,合同金额为300万,实际结算金额也是300万,工程完工,在珠海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开具建筑业发票300万元,缴纳了9万元的营业税、0.63万元的城市维护建设税、0.27万元的教育费附加、0.18万元的地方教育附加,2.4万元的个人所得税、0.09万元的印花税。根据缴纳的税费单据。借: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90000借: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6300借: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2700借:应交税费—应交地方教育附加 1800借:管理费用—税金 24900(2.4万元+0.09万元)贷:库存现金125700贷:其他会计分录同例1.,这里不再叙述。 工程款支付流程是什么呢?如何实现施工单位纳税、建设单位纳税?
工程款支付流程是什么呢?如何实现施工单位纳税、建设单位纳税?工程款支付流程一般为施工单位在工程结算时开具建筑业统一发票,到建设单位结算工程款。
一般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方无需缴纳营业税,需要按照工程合同金额缴纳印花税,待该工程项目出售后需要缴纳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如果自用需要按照房产原值缴纳房产税;
对于施工单位需要就结算的工程价款缴纳营业税和企业获得的利润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总包方有分包企业,缴纳营业税时可以抵扣分包价款。
1、施工单位根据上月完成工程量,填报申请支付表;
2、交总监理工程师审核;
3、建设方审定;
4、项目所在税务部门交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开发票;(也有甲方扣税的)
5、建设方法人代表在发票签字同意支付;
6、建设方财务部门转账支付。
扩展资料:
一般规定
(1)土地增值税只对“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征税,对“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征税。
(2)土地增值税既对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征税,也对转让地上建筑物及其它附着物产权的行为征税。
(3)土地增值税只对“有偿转让”的房地产征税,对以“继承、赠与”等方式无偿转让的房地产,不予征税。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的行为主要包括两种:
①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人将房产、土地使用权赠与“直系亲属或者承担直接赡养义务人”。
②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将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赠与教育、民政和其他社会福利、公益事业。
 中国户籍网姓名查询怎么操作?
中国户籍网姓名查询怎么操作?答案如下:
1、这个只要有身份证就能查到他的姓名及户口所在地。5元一次,手机扣除,不成功不收费。网站真诚为您提供身份证查询服务。
2、立即显示被核查人的身份照片,身份真伪立刻识别!数据准确:身份证查询数据由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提供。
3、身份证查询结果(包括照片查看密码)以短信形式发动到您手机,不用再跑公安局户籍科了,也省了公交费。
拓展资料:户籍
1、户籍,又称户口,是指国家主管户政的行政机关所制作的,用以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也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
2、户籍是对自然人按户进行登记并予以出证的公共证明簿,记载的事项有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亲属、婚姻状况等。它是确定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律文件。
3、登记户口的册籍:古时也称户版、丁籍、黄籍、籍帐。我国户籍制度建立于商朝。
4、据甲骨文记载,商朝已开始实行人口登记制度,有“登人”或“登众”,即临时征集兵员的记载。《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有了人头统计。这可以视为我国户籍登记制度的萌芽。
 五十多岁的人离婚后该如何生活?
五十多岁的人离婚后该如何生活?五十多岁的人离婚后如何生活,说实在话,年过半百多,儿女已长大成人,结婚成家当上祖字辈的人了,在没有特大情况下,尽量不要再离婚了。一单离婚再另找对象结婚,遇到的事情更多,所找的麻烦会很多又很难以解决。我认为如果没有过大难事,还是将就凑合着过好,这样做比什么都强,至于一定要离婚,希望你必须冷静再冷静考虑为好。
如果是男人主张离婚,或许男人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但是,这个小三肯定不会看上这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而是看上了老男人的腰包。已经这个年龄的老男人,他的老婆可能也是一个中年的同龄女人,女人到了这个年龄,虽然没有了靓丽的外表,但是,长期的夫妻感情,是任何其他情感都取代不了的,此时的老男人,如果因为一个小三离婚,那就是他最错误的决定!
假如说这次婚姻如果是头婚的话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年的婚姻了吧。这个时候孩子也长大了,操劳了大半生,身体也逐渐的不行了,往后的日子,都是越来越需要人陪伴照顾的时候了,这个时候选择离婚,恐怕是百害无一利吧。最好还是要善始善终。如果说这不是头婚,是二婚三婚甚至四婚的话,那就好理解了。习惯使然,不是我恶毒,是有人天生就是一身的贱骨头,这种贱不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消失,而是愈演愈烈,这种人注定是要孤老终生,永远得不到爱。
再说了,大半辈子都走过来了,咋就出了这个事呢,当然绝对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还是事出有因的,离婚了别伤心,人还是要活,并且要活得好好的,莫被别人瞧不起,首先过去的让它过去,有计划的好好生活,早睡早起,一日三餐要吃好,好好劳动和工作,衣服整理干净得体,走跟昂首阔步,待人我满面春风,五十不老,有看得来的人就找一个,人都怕孤独,要是一个人走下去,也是挺难的,不再呼别人议论什么,只要自己舒心就行,那个人都希望自己幸福,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一惯风顺的,人走急了也摔跤,没关系,爬起来,前进继续。
 如何办理英语培训班办理英语培训班必须具备四项基本条件:1)在申请设立学校的时候,应当有可靠的合格教师的来源,能够通过聘任专职的或者兼职的教师来保证教育教学任务的完成;2)要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3)学校设立时,必须建立较为健全的内部组织管理机构;4)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除此以外,举办者还要依法办理设立审批等手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各级各类,其履行审批手续也要按相应的级别层次到相应的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有关主管机关审批。履行审批手续的具体程序大致为:1、由举办者向审批机关提出设立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申请书;申请书应当按照有关设置标准载明有关事项;2、由审批机关进行审核,包括到办学场所实地调查了解情况;3、由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有关主管机关批准。
如何办理英语培训班办理英语培训班必须具备四项基本条件:1)在申请设立学校的时候,应当有可靠的合格教师的来源,能够通过聘任专职的或者兼职的教师来保证教育教学任务的完成;2)要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3)学校设立时,必须建立较为健全的内部组织管理机构;4)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除此以外,举办者还要依法办理设立审批等手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各级各类,其履行审批手续也要按相应的级别层次到相应的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有关主管机关审批。履行审批手续的具体程序大致为:1、由举办者向审批机关提出设立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申请书;申请书应当按照有关设置标准载明有关事项;2、由审批机关进行审核,包括到办学场所实地调查了解情况;3、由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有关主管机关批准。 有限合伙企业怎么交所得税?
有限合伙企业怎么交所得税?1.合伙企业所得的分配比例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按照下列原则分配应纳税所得额:
(1)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以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
(2)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人协商决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
(3)协商不成的,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
(4)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以全部生产经营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人数量平均计算每个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
2.合伙企业不是所得税的纳税人
合伙企业不是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如果A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为自然人和法人,A合伙企业作为合伙人再投资设立B合伙企业,应以A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作为纳税人。
3.“先分后税”的原则
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应按先分后税原则,根据分配比例计算各个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包括合伙企业分配给所有合伙人的所得和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利润),不包括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和股息。即为合伙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其中收入总额,是指合伙企业从事生产经营以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活动所取得的各项收入,包括商品(产品)销售收入、营运收入、劳务服务收入、工程价款收入、财产出租或转让收入、利息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营业外收入。
个人合伙人按分配比例计算的所得,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
 店铺装修折旧费怎么算
店铺装修折旧费怎么算店铺装修的费用可以计入长期待摊费用-装修费,按5年分摊计入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装修费用 或者按可以使用的年限分摊。 重置价格要看物价、人工费用的增长情况。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固定资产而使其损耗导致价值减少仅余一定残值,其原值与残值之差在其使用年限内分摊的固定资产耗费是固定资产折旧。确定固定资产的折旧范围是计提折旧的前提。
国民收入账户中也称资本消耗补偿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确定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分摊。使用寿命指固定资产的预计寿命。应计折旧额指应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的原价扣除其预计净残值后的金额。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应扣除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
扩展资料
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是用来生产产品的,也是有成本的。它的价值,就是他的成本,需要计入到产品的成本中去。需要摊销。这就是固定资产为什么要计提折旧的原因。
固定资产折旧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成本摊销的期限不应该仅仅是一年,而是他的使用期限。因此需要合理估计每个期限要摊销的成本,这就是每年的折旧额和摊销额。如果在购买时直接全部摊销,则当年费用很高,利润减少,而以后年度利润高估。这都是会计所不允许的。
固定资产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能够连续在若干个生产周期内发挥作用并保持其原有的实物形态,而其价值则是随着固定资产的磨损逐渐地转移到所生产的产品中去,这部分转移到产品中的固定资产价值,就是固定资产折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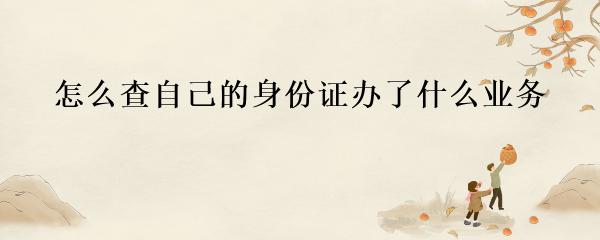 怎么查自己的身份证办了什么业务没有哪个网站能直接查询出你身份证的详细信息或办理的业务的,每项业务都是由每个部门严格管理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拿着证到各个与身份证有关的部门查询,比如:你担心他用你身份证申请了手机卡或电话,你可以到移动公司,联通公司查询。
怎么查自己的身份证办了什么业务没有哪个网站能直接查询出你身份证的详细信息或办理的业务的,每项业务都是由每个部门严格管理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拿着证到各个与身份证有关的部门查询,比如:你担心他用你身份证申请了手机卡或电话,你可以到移动公司,联通公司查询。 摩托车行驶证怎样查询?
摩托车行驶证怎样查询?1、携带驾驶证、行驶证去车管所查询;
2、进入当地交警网,输入车牌号、车架信息就可以查询;
3、查看摩托车行驶证上的检验合格有效期。
摩托车号牌说明:黄色牌照的车辆为两、三轮摩托车,蓝色牌照的汽车为轻便摩托车,发动机号和车辆识别代号在车辆行驶证上。
扩展资料:
注意事项
另外要注意,车主买新车时即使同时购买机动车辆保险,部分保险项目也要在机动车入户和领取《机动车行驶证》之日起才能生效。
新车保修凭证。《机动车行驶证》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能够确定新车“保修期”的起始日期。例如,一汽集团规定该厂生产的汽车保修期限为汽车领取《机动车行驶证》之日起2年和累计行驶4万公里以内,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在此保修期之内,凡是因为制造、装配以及材料质量问题引起的车辆损坏,用户可以凭保修卡、《机动车行驶证》等证件,在该厂的特约服务站免费接受保修服务。
《机动车行驶证》是我国法律、法规认可的重要证件,具有非同小可的作用。机动车驾驶员务必高度重视它,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办理身份证需要录入哪些个人信息补办二代身份证必须录入持证人的指纹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三条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的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指纹信息、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公...。
办理身份证需要录入哪些个人信息补办二代身份证必须录入持证人的指纹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三条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的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指纹信息、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公...。 城市户口如何办理农村房产证农村有宅基地就可以办理。需要去派出所登记申请,需要村里开具证明,证明你的房屋是你的宅基地。需要周围3个方面的第一户邻居同意宅基地属于你。三个方向有一家不同意,宅基地无法申请。
城市户口如何办理农村房产证农村有宅基地就可以办理。需要去派出所登记申请,需要村里开具证明,证明你的房屋是你的宅基地。需要周围3个方面的第一户邻居同意宅基地属于你。三个方向有一家不同意,宅基地无法申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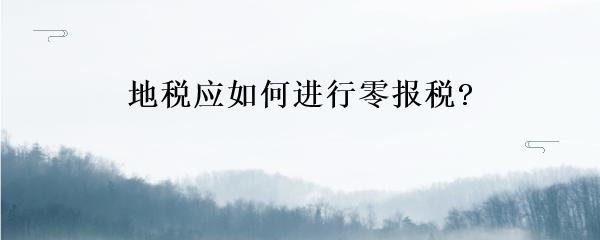 地税应如何进行零报税?
地税应如何进行零报税?地税网上报税零申报的步骤是:
1、打开地税网站,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
2、选择“申报缴纳”,点击“纳税申报”,根据企业实际业务情况进行零申报,提交即可。
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采用信息化、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已成为趋势,远程电子申报纳税是一种先进的申报方式。
扩展资料1、网上申报纳税的企业每月申报期都必须填写《通用纳税申报表》。表中包括本申报期纳税人应当申报的全部税种信息,如税种名称、税目名称、税款所属时期、税率以及税种是否代扣、委托等。
网上报税将各税种以一定形式统一在一张综合表中,并由系统根据各个税种设定计算公式。《通用纳税申报表》中需要纳税人填写的数据是计税依据和允许扣除项目,其他数据项目可由系统根据内定的公式自动计算出来,纳税人也可以修改。
2、网上报税需填写报送的其他纳税申报表如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其中,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是季度报表,必须与《通用纳税申诉表》一并提交,且数字相符,申报才算成功。
3、网上报税还需报送作为财务分析依据的财务报表,以验证报表的平衡及勾稽关系。这些财务报表包括:
(1)资产负债表(月报);
(2)损益表(月报);
(3)应上缴各税及其他款项情况表;
(4)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年报);
(5)利润分配表(年报);
(6)现金流量表(年报)。
4、采用网上报税的业户必须定期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纸质申报资料:
(1)《通用纳税申报表》;
(2)《资产负债表》;
(3)《损益表》;
(4)其他需报送的资料。
纳税人在向税务机关报送纸质资料时,要求必须在每份资料的纳税人名称处加盖单位公章。按照上述列出的需报送资料的顺序定期向办税服务厅报送。
5、网上报税需要办理网上报税手续才能使用,即要签订纳税人、税务机关、纳税专户开户银行三方协议,由税务局分配办理网上报税业务的登陆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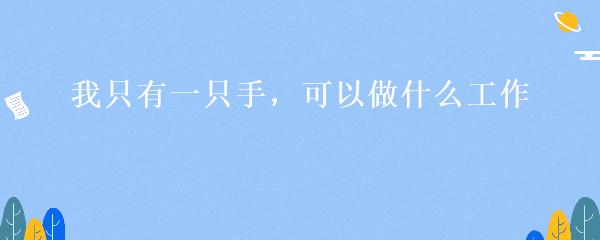 我只有一只手,可以做什么工作一只手可以做很多工作的,我见过一个卖毛笔的人,也是一只手,而且是左手,但是他用左手写的毛笔字比我用右手写的还好!还有一个用木头做各种小珠子的,就是手链上串的那种各种花样的珠子,做的很漂亮,生意也很好。加油!祝福你。
我只有一只手,可以做什么工作一只手可以做很多工作的,我见过一个卖毛笔的人,也是一只手,而且是左手,但是他用左手写的毛笔字比我用右手写的还好!还有一个用木头做各种小珠子的,就是手链上串的那种各种花样的珠子,做的很漂亮,生意也很好。加油!祝福你。 工程签合同的时候都有个让利多少,是什么意思?是对应一定标准的让利,无非是一种好听的说法而已,比如某工程按照当地预算定额计算出来的结果为100万元,这100万元里面是含有利润的,比如说是10万元。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现只要95万元,也就是说本来要赚10万元,现在把其中的5万无利润让出来给对方,就是这个意思。
工程签合同的时候都有个让利多少,是什么意思?是对应一定标准的让利,无非是一种好听的说法而已,比如某工程按照当地预算定额计算出来的结果为100万元,这100万元里面是含有利润的,比如说是10万元。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现只要95万元,也就是说本来要赚10万元,现在把其中的5万无利润让出来给对方,就是这个意思。 oppor9m是什么意思R9m是一款中高端全网通触摸智能手机,m是全网通的意思。R9m主卡支持移动电信2G/3G/4G,联通3G/4G,副卡支持移动电信2G,不支持同时使用2张电信卡。
oppor9m是什么意思R9m是一款中高端全网通触摸智能手机,m是全网通的意思。R9m主卡支持移动电信2G/3G/4G,联通3G/4G,副卡支持移动电信2G,不支持同时使用2张电信卡。 贷款买车必须要有驾驶证吗?
贷款买车必须要有驾驶证吗?贷款买车车主不需要有驾驶证。
在购买汽车进行机动车登记时也不需要车主的驾驶证,只需要车主的身份证即可。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条 申请注册登记的: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
(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
(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六)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
买车注意事项:
1、检查车辆的有关手续,购车发票、购置税、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保养手册、保险单,注意车身VPN鉴别码,发动机号、车架号是不是一致,还有生产日期。
2、核对完车辆信息后,检查车身外观是不是有色差或者刮划痕迹,检查轮胎。
3、检查内饰、配置、看看是不是与自己想要购买的车型标配一致,还有检查随车说明书以及随车工具、警示牌、千斤顶等等。
 房子不能过户是为什么
房子不能过户是为什么房子不能过户是的原因是:
1.未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
2.只取得使用权的房屋,如房屋管理局直管公房;
3.鉴定为危房的房屋,以标准价购买,尚未按成本价补足剩余价款,向全产权过渡的房屋;
4.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兴建的房屋;
5.已经被列入拆迁公告范围的房屋等。
【法律依据】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条,房地产权利人应当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法纳税。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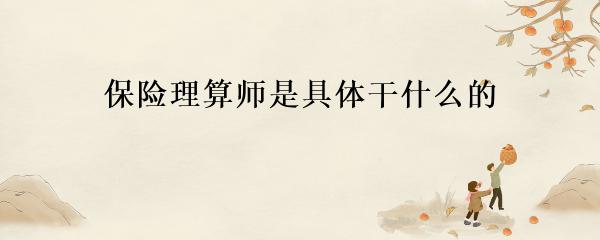 保险理算师是具体干什么的保险理算,是为保险产品做规划的,一般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总精算师。做这个职位的很多,带证上岗的不到一百人,也就是全国没有几个保险公司有这样的人。
保险理算师是具体干什么的保险理算,是为保险产品做规划的,一般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总精算师。做这个职位的很多,带证上岗的不到一百人,也就是全国没有几个保险公司有这样的人。 拍白底一寸照片穿什么颜色衣服好看
拍白底一寸照片穿什么颜色衣服好看黑色、红色、黄色。
如果是拍白底的寸照,一定不能穿白色的衣服,要穿颜色稍微深点的衣服,这样才能跟白底形成明显的对比。比如黑色、红色、黄色等。最好穿有领的衬衫,这样拍出来的照片会比较正式一点,还可以穿黑色外套搭配白衬衫,这样白衬衫就不会跟白底融合在一起。
扩展资料:
用户拍证件照注意事项:
证件照还有多种规格可选,一寸证件照,二寸证件照,大学报名电子照,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件照,教师资格证照片,司法考试证件照,英语四六级证件照,驾驶证证件照等等,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衣服最好是深色衣服,但一定不能和背景相同,头发比较毛躁,可以沾水抚平,可以尝试不戴眼镜或者戴镜框拍摄,最好用手机后置摄像头拍摄,距离摄像头约6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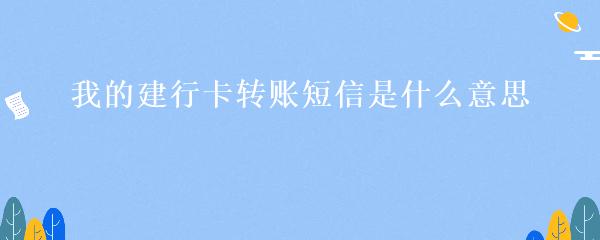 我的建行卡转账短信是什么意思那是你开通了建行的短信银行服务.你办的是包月的,2元/月.就是说你的账户金额发生变动就会收到一条短信.不是年费,是单独收取的.在你的建行卡上收取.每月初收取一次。
我的建行卡转账短信是什么意思那是你开通了建行的短信银行服务.你办的是包月的,2元/月.就是说你的账户金额发生变动就会收到一条短信.不是年费,是单独收取的.在你的建行卡上收取.每月初收取一次。




 微信
微信
 微博
微博
 QQ空间
QQ空间
 复制网址
复制网址
